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你好,我是刘瑜,欢迎来到比较政治学节目,今天是第21讲。
前面我们花了好几集的节目谈论国家能力的来源,我们谈到了战争、文官制、社会运动等等因素的作用,不过,谈论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论国家建构比较成功的案例,欧洲、中国、美国。今天,我却想谈论一个“失败国家”:阿富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学要避免“优胜者偏见”,要把失败者也带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做出平衡的分析。在国家能力方面,阿富汗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案例。
一
说到阿富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恐怖袭击、贫困、落后。没错,这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阅读阿富汗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对于我们中国人,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生活是颇为动荡的,但是1978年之后,过去四十多年,生活大体而言不断改善。而阿富汗的经历刚好相反,在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大体平静的,连一战、二战都没有卷入。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6、70年代喀布尔的照片,比如我们文稿里这两张图片(图1和图2),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但是1978年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40年来,阿富汗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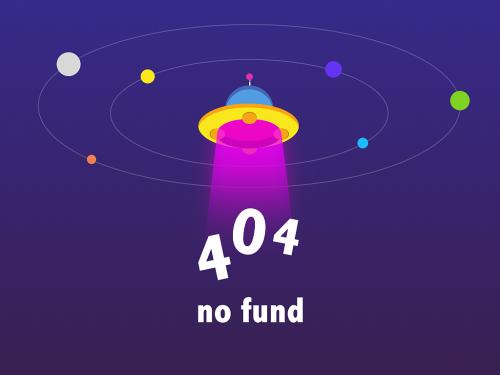
1978年,阿富汗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在这场被称为“沙尔革命”的政变中,极左的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伍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激进左翼政权,从此开启了阿富汗的噩梦模式。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达伍德1973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当时,他认为王室过于保守,而他希望推动更加左翼的社会变革,所以推翻了阿富汗王室,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结果5年之后,他本人又被更左翼的人民民主党推翻,结局可以说非常反讽。
1978年沙尔革命后,人民民主党上台,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没想到阿富汗人民并不领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新政权很快挺不住了,于是向苏联求援。1979年,苏军开着坦克就进来了,战争由此开始:一边是政府及其后台苏军,一边则是武装民众。本来,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民众,怎么可能打得过苏联的飞机大炮?但是,适逢冷战高峰,阿富汗的武装民众背后涌现出一批热情的大哥: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也正是在这时候,本拉登毅然抛弃了他在沙特的富豪生活,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来到了阿富汗。所以,在他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前,他确实曾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于是,在所有这些力量的搅和下,一场本来可能短平快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噩梦。
1989年苏东巨变,苏联撤军。事实证明,苏联的入侵是一个悲剧,苏联的撤退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苏军撤离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勉强挣扎了3年,于1992年垮台。本来,这是阿富汗结束战争、回归常态的机会。事实上,苏联倒台、冷战结束后,有一批陷入左右内战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结束了内战,毕竟,老大哥都不在了,小弟们也不用再打了。但是,阿富汗却回不去了。1992到1996年,当初共同抵抗苏联的武装组织开始相互厮杀。如果和苏联的战斗只是摧毁了半个阿富汗,苏联撤离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另外半个阿富汗。也是在这个阶段,喀布尔被打回了石器时代。
混乱的内战,最后的确产生了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胜利者,而是奇葩的塔利班。本来,凶残如塔利班,即使不能构建一个美好的国家,也能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但是,因为塔利班太奇葩了,各种倒行逆施,导致原先相互厮杀的小伙伴们纷纷团结起来与它对抗,这就是著名的“北方联军”。因此,即使塔利班上台,阿富汗内战还在继续,直到2001年塔利班被美军推翻。据估算,1978年到2001年,阿富汗大约有100-200万人战死,有400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数百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对于一个总人口3000万左右的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2001年美军入侵,一度被视为阿富汗的转机。然而,正如20年前的苏联,美军也逐渐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2001年,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但是很快,塔利班卷土重来,到2019年,政府只控制着35%的领土,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的土地,而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图3)。

与此同时,因为安全局势的恶化,其它所有的治理维度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到2020年,阿富汗的贫困率高达人口的一半,鸦片成为阿富汗的支柱性产业,10%的人口吸毒,80%的阿富汗人表示害怕在境内旅行,2/3的人表示害怕投票。为什么害怕投票?因为塔利班屡次袭击投票站。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政府。事实上,塔利班和美国谈判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阿富汗政府参加谈判。一个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政府,谈何国家能力。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我们发现,阿富汗过去40年的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注意,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不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个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一样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二
但也正是因为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失败,也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窗口,去观察国家建构的各种阻碍性因素。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因素。对这四个因素的分析,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它“失败国家”的失败原因。
首先是地理条件。大家不要觉得,自然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之大。在比较政治学的内战研究中,许多研究都会把“多山与否”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为什么?因为多山意味着政府触角的限度,也意味着叛军容易找到藏身之所。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大家可以看看解说词中的阿富汗地势图(图4图5)。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可以想象,在这种地形地势中,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是非常困难的,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种地貌,出门买个菜看上去都像是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


所以,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就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直到1747年,阿富汗才建立了以当地人认同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这也就是延续了200多年、1973年被达伍德推翻的杜兰尼王朝。大家注意,1747年,这在中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是中华王朝帝国的尾声了。但是,对于阿富汗,这时候它的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始。即使是杜兰尼王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统治,王室所真正控制的,仅仅是几个大城市而已,其它地方,主要还是各部落长老说了算。
所以,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听上去似乎阿富汗人多么厉害,仔细想想,其实阿富汗最厉害的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山。我们都知道,1842年,英国在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但是同一年,大英帝国在阿富汗却遭遇了惨败。为什么?因为海战是英国的长项,而在山上打游击,英国人不会啊。最后,在阿富汗冬天的群山之中,上万英国人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2001年美军入侵,也是发现,他们的武器再先进,面对这种延绵不绝的山脉难以发挥威力。道理很简单:你根本找不到敌人。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出则为战士,退则为农民,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问题在于,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好,说完了地形地貌,我们再来说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这个障碍还是与地理有关,就是它的地缘位置。自古以来,阿富汗地区都被大国强国包围,北边是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西边是伊朗和阿拉伯帝国,东北方向时不时出现蒙古帝国这样的游牧帝国,东南方向则是印度以及一度占领印度的大英帝国。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所以很自然地,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这就像张三和李四打架,可怜的小明偏偏住在他们两家中间,谁也不招惹,家里却总是被砸得稀巴烂。我们之前说,战争缔造国家,但问题在于,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为什么?这就有点像骑车。骑车是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不是自主发力,而是靠电池发力,那么骑的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
更糟的是,因为是代理战争,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本来阿富汗这样一个小国,内战很容易打完,决出胜负之后就实现暴力垄断了。但问题是,身处大国的包围圈,这些外国势力不让你打完。这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9年快倒了,苏联开着坦克进来了,帮它续命。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民主党本来可以搞定阿富汗,但是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进来了,帮圣战战士续命。1996年,塔利班已经建立政权了,但是美军又开着飞机过来了,赶跑了塔利班。2001年塔利班已经被赶跑了,一个准民主政体建立了,巴基斯坦那边的极端分子又打开了怀抱,又开始给塔利班续命。所以,本来可能三、五年能打完的内战,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干预,就变得没完没了,怎么也打不到句号。大家想想,如果当年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刚要打赢,一会儿罗马帝国突然跑出来扶持韩魏赵,一会儿波斯帝国跑来扶持吴楚越,秦国的建国大业是不是就变得遥遥无期?幸亏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离得太远了,所以战争能打上句号。所以,地缘因素,是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是宗教。确切地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其实,历史上,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但是,两股力量的对撞,在阿富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第一股力量,是苏军入侵。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圣战战士”。可以说,阿富汗的宗教热情真的是被苏联捅马蜂窝捅出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另一股势力,这些圣战组织虽然有宗教名目,但本质上也只是军事力量,它们只是想赶跑苏军,未必想用“宗教理想国”来改造阿富汗社会。另一股力量是什么?是萨拉菲主义。什么是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到1970年代末期,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
为什么巴基斯坦的萨拉菲主义会煽动起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为什么上宗教学校?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教育,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而这些宗教学校教什么?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于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了。苏军撤退后,他们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当时,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因为对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塔利班上台后,其所作所为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禁止音乐、电影和娱乐,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用石头砸同性恋,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听众朋友中可能有人读过《追风筝的人》,里面就说到,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如果不是这种“进口的”宗教极端主义,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归1978年之前的样子,但是,阿富汗再也回不去了。
尽管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但是塑造了它、以及它所塑造的极端主义文化,却开始浸润阿富汗的土壤,有可能在几代人之间,都不会完全消失。2013年皮尤中心有个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穆斯林对自杀袭击的看法,阿富汗人中表示“自杀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正当的”的比例高达39%,几乎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另一项民调中,当问及政治和宗教是否应该分离时,57%的阿富汗人表示不应该,宗教领袖应当介入政治。此类数字不仅仅是数字,它会转化为真实的悲剧。2010年《时代》杂志封面登出过一个阿富汗女性的照片,大家从文稿中也能看到这个照片(图6)。这个女性叫bibi aisha,生活在塔利班占领区,丈夫也是一个塔利班。因为数次从虐待她的丈夫家里逃跑,被丈夫亲手割掉了鼻子和耳朵,被扔到山上去等死,死里逃生后,才有了这个照片。所以,极端主义不仅仅是纸上的条文,它背后是无数悲惨的人生。

2001年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像南非当年一样,实现权力分享吗?答案是:不能。至少,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答案就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的和最高的法,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只能臣服于伊斯兰法。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纯粹的权力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余地。
妨碍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四个障碍,则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曾经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但是,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比如,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造就了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但是对其原先的母国南斯拉夫来说,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离心力。希腊的民族主义使其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成就了现代希腊,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希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国家建构的绊脚石。
阿富汗是个地地道道的多民族国家。文稿中可以看到阿富汗大致的族群分布(图7):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占人口大约40%;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占大约25%;哈扎拉人,10%左右,乌兹别克人,10%。此外还有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则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比如,阿富汗虽然只有1500万普什图人,但是在国界线的南边,巴基斯坦有3500万左右普什图人,相当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娘家就住在隔壁。以此类推,塔吉克人受到塔吉克斯坦的支持,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受到伊朗的支持。这种情况下,任何族群想要吃掉其它族群,都往往望而却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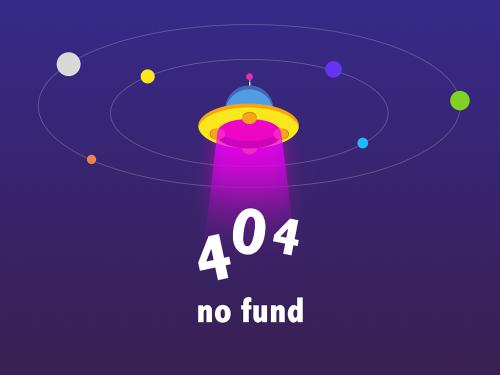
其实,现代史上,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并不算严重,没有显著的分离主义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多山地形以及由此形成的部落主义传统,不但消解了帝国、消解了国家、甚至消解了民族。我就是某某村的,“民族”是什么?还是太抽象了、太宏大了。但是,1979苏军入侵,不但动员出了阿富汗人的宗教热情,也动员出了他们的民族热情。原因很简单,以民族为基础进行军事动员,最有效率。
所以,我们看到,在苏军占领期间,虽然阿富汗几乎全民抵抗,但是抵抗的力量却是分片包干的。塔吉克人由著名的“北方雄狮”马苏德领导;乌兹别克人靠dostam领导;普什图人最后大体聚集到了hekmatyar手下;哈扎拉人也在自己的领地上抗战。这种“包干区”式的抵抗有其严重后果,那就是苏联被赶跑后,他们内部就开始为“胜利果实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大打出手。这就有点像国共合作打日本,日本一跑,国共自己就打起来了。只不过,在40年代的中国,内战是两军对垒,但是1989年之后的阿富汗,可不止两股势力,而是四、五股势力。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和平协议太难了,因为否决点太多,只要一方不合作,其它三、四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就会被作废。也正是这种碎片化的状态,给了塔利班可乘之机。
今天,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也和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相关。塔利班从普什图地区起家、其成员主要是普什图族,其藏身之处也主要在普什图地区。有民调显示,尽管在整个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只有15%左右,但是在部分普什图省份,这个比例可以高达50%左右。正是普什图族提供的这种人员、物资、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统,使得塔利班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存活下来并东山再起。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则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任何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得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三
阿富汗的困境也帮助我们分析其它国家的国家建构瓶颈。无论是特定的地形地势、地缘环境,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主义,都广泛存在于许多其它国家,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把这些因素合而为一,也因此沦落为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失败国家”之一。
不过,阿富汗的国家建构真的完全无可救药吗?也未必。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特定的地理因素虽然使中央集权式国家难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结构也未必不可行。仔细分析,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漩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这两种极端主义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主义、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于高度极权。在这个过程中,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其实,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5%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其实,岂止阿富汗面临这样的危险,在一个日渐极化的世界中,哪个国家不是如此?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刘瑜,欢迎来到比较政治学节目,今天是第21讲。
前面我们花了好几集的节目谈论国家能力的来源,我们谈到了战争、文官制、社会运动等等因素的作用,不过,谈论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论国家建构比较成功的案例,欧洲、中国、美国。今天,我却想谈论一个“失败国家”:阿富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头,我就说过,比较政治学要避免“优胜者偏见”,要把失败者也带入比较的视野,才能做出平衡的分析。在国家能力方面,阿富汗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案例。
一
说到阿富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战火、恐怖袭击、贫困、落后。没错,这确实是个非常悲剧的国家。阅读阿富汗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对于我们中国人,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生活是颇为动荡的,但是1978年之后,过去四十多年,生活大体而言不断改善。而阿富汗的经历刚好相反,在整个20世纪,1978年之前,他们的生活是大体平静的,连一战、二战都没有卷入。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6、70年代喀布尔的照片,比如我们文稿里这两张图片(图1和图2),那时候的喀布尔街道秩序井然,女性时尚现代,整个国家朝气蓬勃,但是1978年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40年来,阿富汗再也没有目睹过真正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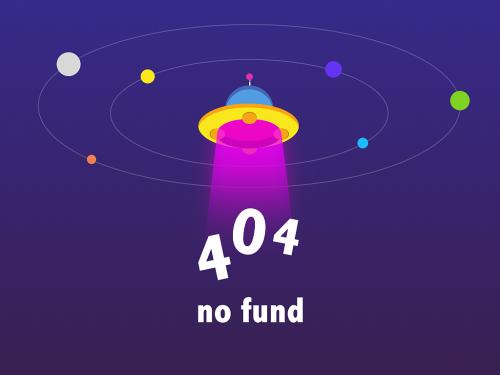
1978年,阿富汗发生了什么?一场政变。在这场被称为“沙尔革命”的政变中,极左的人民民主党推翻了达伍德政府,建立了一个激进左翼政权,从此开启了阿富汗的噩梦模式。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达伍德1973年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当时,他认为王室过于保守,而他希望推动更加左翼的社会变革,所以推翻了阿富汗王室,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结果5年之后,他本人又被更左翼的人民民主党推翻,结局可以说非常反讽。
1978年沙尔革命后,人民民主党上台,开始推行更激进的改革,但是,没想到阿富汗人民并不领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新政权很快挺不住了,于是向苏联求援。1979年,苏军开着坦克就进来了,战争由此开始:一边是政府及其后台苏军,一边则是武装民众。本来,根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的民众,怎么可能打得过苏联的飞机大炮?但是,适逢冷战高峰,阿富汗的武装民众背后涌现出一批热情的大哥: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也正是在这时候,本拉登毅然抛弃了他在沙特的富豪生活,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来到了阿富汗。所以,在他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之前,他确实曾是美国的亲密战友。于是,在所有这些力量的搅和下,一场本来可能短平快的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噩梦。
1989年苏东巨变,苏联撤军。事实证明,苏联的入侵是一个悲剧,苏联的撤退则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苏军撤离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勉强挣扎了3年,于1992年垮台。本来,这是阿富汗结束战争、回归常态的机会。事实上,苏联倒台、冷战结束后,有一批陷入左右内战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结束了内战,毕竟,老大哥都不在了,小弟们也不用再打了。但是,阿富汗却回不去了。1992到1996年,当初共同抵抗苏联的武装组织开始相互厮杀。如果和苏联的战斗只是摧毁了半个阿富汗,苏联撤离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另外半个阿富汗。也是在这个阶段,喀布尔被打回了石器时代。
混乱的内战,最后的确产生了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只不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胜利者,而是奇葩的塔利班。本来,凶残如塔利班,即使不能构建一个美好的国家,也能构建一个有效的国家,但是,因为塔利班太奇葩了,各种倒行逆施,导致原先相互厮杀的小伙伴们纷纷团结起来与它对抗,这就是著名的“北方联军”。因此,即使塔利班上台,阿富汗内战还在继续,直到2001年塔利班被美军推翻。据估算,1978年到2001年,阿富汗大约有100-200万人战死,有400万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数百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对于一个总人口3000万左右的国家,这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2001年美军入侵,一度被视为阿富汗的转机。然而,正如20年前的苏联,美军也逐渐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2001年,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但是很快,塔利班卷土重来,到2019年,政府只控制着35%的领土,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的土地,而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图3)。

与此同时,因为安全局势的恶化,其它所有的治理维度都不可能真正改善。到2020年,阿富汗的贫困率高达人口的一半,鸦片成为阿富汗的支柱性产业,10%的人口吸毒,80%的阿富汗人表示害怕在境内旅行,2/3的人表示害怕投票。为什么害怕投票?因为塔利班屡次袭击投票站。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政府。事实上,塔利班和美国谈判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阿富汗政府参加谈判。一个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政府,谈何国家能力。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当代简史,我们发现,阿富汗过去40年的灾难延绵不绝,在所有可能逃离灾难的出口,阿富汗都错过了。注意,在我刚才描述的简史中,不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某一个政体难以建构暴力垄断的国家,而是任何政府、任何政体都难以建构国家。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一样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二
但也正是因为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失败,也给了我们一个理论窗口,去观察国家建构的各种阻碍性因素。为什么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如此之难?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因素。对这四个因素的分析,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它“失败国家”的失败原因。
首先是地理条件。大家不要觉得,自然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之大。在比较政治学的内战研究中,许多研究都会把“多山与否”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为什么?因为多山意味着政府触角的限度,也意味着叛军容易找到藏身之所。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大家可以看看解说词中的阿富汗地势图(图4图5)。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可以想象,在这种地形地势中,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是非常困难的,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种地貌,出门买个菜看上去都像是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


所以,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就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直到1747年,阿富汗才建立了以当地人认同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这也就是延续了200多年、1973年被达伍德推翻的杜兰尼王朝。大家注意,1747年,这在中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是中华王朝帝国的尾声了。但是,对于阿富汗,这时候它的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始。即使是杜兰尼王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统治,王室所真正控制的,仅仅是几个大城市而已,其它地方,主要还是各部落长老说了算。
所以,把阿富汗叫做“帝国的坟场”,听上去似乎阿富汗人多么厉害,仔细想想,其实阿富汗最厉害的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山。我们都知道,1842年,英国在中国打赢了鸦片战争,但是同一年,大英帝国在阿富汗却遭遇了惨败。为什么?因为海战是英国的长项,而在山上打游击,英国人不会啊。最后,在阿富汗冬天的群山之中,上万英国人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后来1979年苏军入侵、2001年美军入侵,也是发现,他们的武器再先进,面对这种延绵不绝的山脉难以发挥威力。道理很简单:你根本找不到敌人。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出则为战士,退则为农民,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问题在于,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好,说完了地形地貌,我们再来说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这个障碍还是与地理有关,就是它的地缘位置。自古以来,阿富汗地区都被大国强国包围,北边是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西边是伊朗和阿拉伯帝国,东北方向时不时出现蒙古帝国这样的游牧帝国,东南方向则是印度以及一度占领印度的大英帝国。因为地处这些大国的交界地带,所以很自然地,它就成为大国征战的通道。这就像张三和李四打架,可怜的小明偏偏住在他们两家中间,谁也不招惹,家里却总是被砸得稀巴烂。我们之前说,战争缔造国家,但问题在于,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为什么?这就有点像骑车。骑车是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不是自主发力,而是靠电池发力,那么骑的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
更糟的是,因为是代理战争,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本来阿富汗这样一个小国,内战很容易打完,决出胜负之后就实现暴力垄断了。但问题是,身处大国的包围圈,这些外国势力不让你打完。这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79年快倒了,苏联开着坦克进来了,帮它续命。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民主党本来可以搞定阿富汗,但是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进来了,帮圣战战士续命。1996年,塔利班已经建立政权了,但是美军又开着飞机过来了,赶跑了塔利班。2001年塔利班已经被赶跑了,一个准民主政体建立了,巴基斯坦那边的极端分子又打开了怀抱,又开始给塔利班续命。所以,本来可能三、五年能打完的内战,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干预,就变得没完没了,怎么也打不到句号。大家想想,如果当年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刚要打赢,一会儿罗马帝国突然跑出来扶持韩魏赵,一会儿波斯帝国跑来扶持吴楚越,秦国的建国大业是不是就变得遥遥无期?幸亏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离得太远了,所以战争能打上句号。所以,地缘因素,是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二个障碍。
第三个障碍,是宗教。确切地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其实,历史上,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但是,两股力量的对撞,在阿富汗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第一股力量,是苏军入侵。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圣战战士”。可以说,阿富汗的宗教热情真的是被苏联捅马蜂窝捅出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另一股势力,这些圣战组织虽然有宗教名目,但本质上也只是军事力量,它们只是想赶跑苏军,未必想用“宗教理想国”来改造阿富汗社会。另一股力量是什么?是萨拉菲主义。什么是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到1970年代末期,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
为什么巴基斯坦的萨拉菲主义会煽动起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为什么上宗教学校?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教育,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而这些宗教学校教什么?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于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了。苏军撤退后,他们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当时,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因为对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塔利班上台后,其所作所为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把已经进入职场和学校的女性重新赶回家门、强迫所有的女性蒙面、禁止音乐、电影和娱乐,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恢复了很多伊斯兰教中古老的刑罚,比如用砍手来惩罚盗窃,用石头砸同性恋,公开虐待和处决罪犯。听众朋友中可能有人读过《追风筝的人》,里面就说到,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如果不是这种“进口的”宗教极端主义,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归1978年之前的样子,但是,阿富汗再也回不去了。
尽管塔利班2001年被推翻,但是塑造了它、以及它所塑造的极端主义文化,却开始浸润阿富汗的土壤,有可能在几代人之间,都不会完全消失。2013年皮尤中心有个民意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穆斯林对自杀袭击的看法,阿富汗人中表示“自杀袭击常常或有时是正当的”的比例高达39%,几乎是所有被调查国家中最高的。另一项民调中,当问及政治和宗教是否应该分离时,57%的阿富汗人表示不应该,宗教领袖应当介入政治。此类数字不仅仅是数字,它会转化为真实的悲剧。2010年《时代》杂志封面登出过一个阿富汗女性的照片,大家从文稿中也能看到这个照片(图6)。这个女性叫bibi aisha,生活在塔利班占领区,丈夫也是一个塔利班。因为数次从虐待她的丈夫家里逃跑,被丈夫亲手割掉了鼻子和耳朵,被扔到山上去等死,死里逃生后,才有了这个照片。所以,极端主义不仅仅是纸上的条文,它背后是无数悲惨的人生。

2001年后,这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成为阿富汗国家建构最大的障碍。我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塔利班一定要和政府打?他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就像南非当年一样,实现权力分享吗?答案是:不能。至少,如果现在的塔利班还是过去的塔利班,答案就是“不能”。为什么?因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刚性。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法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的和最高的法,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只能臣服于伊斯兰法。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纯粹的权力之争可以讨价还价,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余地。
妨碍阿富汗国家建构的第四个障碍,则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它曾经是许多单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动力,但是,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又往往是国家建构的离心力。比如,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造就了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但是对其原先的母国南斯拉夫来说,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离心力。希腊的民族主义使其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成就了现代希腊,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希腊的民族主义显然是国家建构的绊脚石。
阿富汗是个地地道道的多民族国家。文稿中可以看到阿富汗大致的族群分布(图7):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占人口大约40%;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占大约25%;哈扎拉人,10%左右,乌兹别克人,10%。此外还有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则是这些民族周边,都有其族群的大本营国家。比如,阿富汗虽然只有1500万普什图人,但是在国界线的南边,巴基斯坦有3500万左右普什图人,相当于一个势力强大的娘家就住在隔壁。以此类推,塔吉克人受到塔吉克斯坦的支持,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受到伊朗的支持。这种情况下,任何族群想要吃掉其它族群,都往往望而却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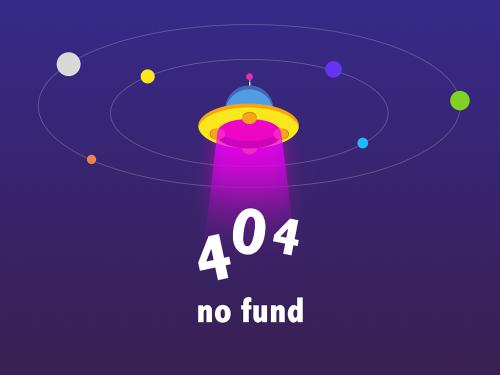
其实,现代史上,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并不算严重,没有显著的分离主义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多山地形以及由此形成的部落主义传统,不但消解了帝国、消解了国家、甚至消解了民族。我就是某某村的,“民族”是什么?还是太抽象了、太宏大了。但是,1979苏军入侵,不但动员出了阿富汗人的宗教热情,也动员出了他们的民族热情。原因很简单,以民族为基础进行军事动员,最有效率。
所以,我们看到,在苏军占领期间,虽然阿富汗几乎全民抵抗,但是抵抗的力量却是分片包干的。塔吉克人由著名的“北方雄狮”马苏德领导;乌兹别克人靠dostam领导;普什图人最后大体聚集到了hekmatyar手下;哈扎拉人也在自己的领地上抗战。这种“包干区”式的抵抗有其严重后果,那就是苏联被赶跑后,他们内部就开始为“胜利果实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大打出手。这就有点像国共合作打日本,日本一跑,国共自己就打起来了。只不过,在40年代的中国,内战是两军对垒,但是1989年之后的阿富汗,可不止两股势力,而是四、五股势力。这种情况下,要达成和平协议太难了,因为否决点太多,只要一方不合作,其它三、四方好不容易达成的协议就会被作废。也正是这种碎片化的状态,给了塔利班可乘之机。
今天,塔利班能够卷土重来,也和普什图人的民族主义相关。塔利班从普什图地区起家、其成员主要是普什图族,其藏身之处也主要在普什图地区。有民调显示,尽管在整个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只有15%左右,但是在部分普什图省份,这个比例可以高达50%左右。正是普什图族提供的这种人员、物资、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统,使得塔利班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存活下来并东山再起。
所以,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则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任何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得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三
阿富汗的困境也帮助我们分析其它国家的国家建构瓶颈。无论是特定的地形地势、地缘环境,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主义,都广泛存在于许多其它国家,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把这些因素合而为一,也因此沦落为当今世界上最顽固的“失败国家”之一。
不过,阿富汗的国家建构真的完全无可救药吗?也未必。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证明。特定的地理因素虽然使中央集权式国家难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结构也未必不可行。仔细分析,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漩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这两种极端主义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主义、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这种冲动摧毁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却发现在人心面前,暴力会抵达它的限度。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于高度极权。在这个过程中,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其实,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5%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其实,岂止阿富汗面临这样的危险,在一个日渐极化的世界中,哪个国家不是如此?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