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喧闹纷争的美国大选季即将结束,但是2016年大选的影响将长期存在。美国政治的观察家们担心此次大选反映的美国选民在政见上的分歧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都无法愈合。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2016大选是否会产生政党重新洗牌或者政党重组 (party realignment),从而长期改变美国两大政党的选民基础,使得极端意识形态回归到常规政治。
“政党重组”这个术语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v. o. key在1955年一篇文章中提出,是针对他所说的“关键选举”(critical elections)而言,这些选举“展现了现存选民分裂基础的巨大改变”[1]。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美国政治的周期循环:一段时期稳定的选举联盟(electoral coalition)。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一系列新议题的产生,大批选民的意愿发生改变。政党内部发生分歧。最终导致一场“关键选举”,拉开一段新的政治稳定时期的帷幕。总体上来说,美国两党体制趋向保守,所以很多政治学者认为,在常态政治和关键或重组选举之间的混乱与骚动,正是这种保守体制对人们在变革时代的政治诉求的应答。
每一次选举或政党重组一般会产生长达30-40年的改变。在美国历史上,政治学者至少发现了六次政党重组,最近发生的一次是在1980年代初,即所谓的“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问题是,2016年大选之后,美国会经历第七次政党重组吗?
不同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美国不会迎来第七次政党重组,因为在推动两大党对立的核心问题上,诸如种族、性别、福利、税收政策,两党的基本面立场并没有改变。我们再看一下美国选区地图,红蓝相间的版图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持着原先的模样。因此,在julia azari看来,2016大选至多“重新校准一些新议题受到关注后的政治方向,但是两大政党的选民阵营基本不受影响”[2]。
而很多别的学者不同意她的看法。他们预测美国政治将面临一系列基本层面的改变。我们可以说,美国社会在可以遇见的将来将进入一个“非常规政治”期(abnormal politics)。非常规政治的一大特征就是极端的党派性偏见(partisanship)和不稳定的选民联盟。在非常规政治时期,旧有的左派、右派或自由、保守的标签已经不再能够描述两党的派系差别。相反,我们发现右翼政客正在动员传统上是民主党稳定票仓的工人阶层,而民主党的政客则进入深红地带[3],企图策反主流保守派选民。政客之间激烈竞争,把温和中间派的选民推向两极,对大家熟悉的所谓“中间选民理论”(the medium voter thesis)构成挑战。中间选民理论认为,政客们一般都会向中间靠拢,选择温和将极力拉拢中间派,因为选民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呈正态分布。2016年的选举并非如此,特朗普不遗余力地动员共和党的右翼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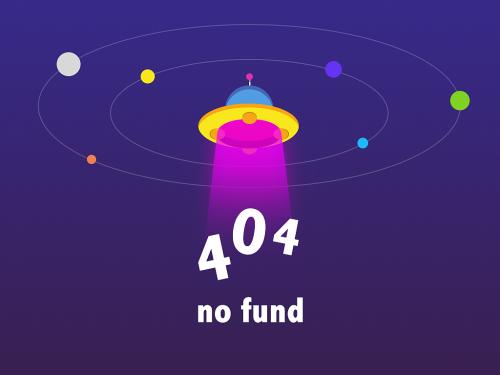
(商界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都站到希拉里一边)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2016年的非常规政治是美国选举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预兆。从民主党方面看,蓝领白人持续不断地流向共和党阵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特朗普的反贸易和反移民政策所诱惑。从共和党方面看,许多比较自由派的利商主义者都被特朗普的粗鄙而吓退,大量传统的共和党成员,包括商界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都站到希拉里一边。过一段时间,两党内部的震荡和混乱也许会平息下去,但在此同时,它可能会导致选民基本面的改变,久而久之,这种基本面的变化会改变两党所代表的利益结构。
单从白人选民在两党之间互换这件事,我们也许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些变化在数目上会有利于哪个党派?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变化可以改变两个政党的特性。试想一个萎缩着的工人阶层,现在因为种族的原因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种族身份认同就会作为一项政治诉求走向台前,而不是经济利益。2016年,低教育的白人工人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投票。相反的,因为特朗普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白人利益和身份的保护者,他们就将自己的命运与特朗普拴在一起,以期通过他来对抗移民、少数族裔和外国劳工。而对于民主党来说,受到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界精英大量涌入,必定会使其右倾,从一个倾向劳工阶层的政党转向为在经济社会政策上更加中性的政党。
那这次的选民重新站队会不会是一时一地的短暂现象?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特朗普吗?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美国社会在人口、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变化标志着未来的两党政治将面临重新洗牌。
首先,美国人口结构改变的趋势将有利于民主党,但是也意味着族群政治危机的加剧。许多研究表明美国选民中种族构成从1988年开始就朝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到2016年,非裔、西班牙裔、亚裔已经占总选民人数的31%。加上女性、拥有高等学历的白人和年轻选民,民主党将在未来几年内有效地扩大其选民基础。这个趋势早在特朗普涉足政坛前就已经出现,特朗普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攻击则加速了共和党选民的大批离去。与此同时,由于共和党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它将为美国的一部分白人本土主义者 (nativists)提供舞台,宣泄其对外国移民、少数族裔甚至建制派精英(establishment)的不满和抵制。
其次,美国乡村与城市、沿海与内陆、小城镇与大都市等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差距在过去20年间持续拉大。倾向于自由的地区越发自由,而倾向于保守的地区则越发保守,美国越来越多的郡县持续由一个政党占据绝对优势。这些郡县可以被称作是选票“悬殊郡县”(landslide counties),也就是说,在这些郡县,要么民主党,要么共和党通常会获得20%以上的压倒性胜利,而不是票数接近。据纽约时报,美国居住在“悬殊郡县”的选民数量从1992年的38%增加到2012年最近一次总统大选中的50%[4]。与此同时,一个日益清晰的两党选票版图正在形成,来自乡村、小镇和所谓“旧经济”地区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而那些来自人口稠密、文化多元的都市选民更偏向于支持民主党。随着两党的分野在地理上变得格外清晰,民主党地区变得更蓝,共和党地区变得更红,美国两党对立的极化政治有了区域化的基础。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的政治分歧的强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的美国大选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也是影响未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性可以和英国脱欧相比。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谁得益、谁受损,从来就是个政治问题。但是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到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其中的因果关联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经济学家gordon hanso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那些受到贸易负面影响的地区更倾向于投票给思想极端的政客[5]。所以,特朗普作为政客不是特例,他不过是在迎合经济民粹主义者反贸易、反移民的诉求。
上述分析表明,因为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2016年美国大选所展露的非常态政治极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对美国政治体制将是一个考验。即便2016年本身不会成为政党重组的关键选举年,两党选民的互换,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混乱,表明我们也许会看到又一轮的美国政党重新洗牌。
注释:
1. v. o. key,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thejournal of politics, 1955, vol. 17, no. 1, p. 4.
2. julia azari, “trump may bring a republicanrecalibration, not a realignment” (retrieved on october 30, 2016: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rump-may-bring-a-republican-recalibration-not-a-realignment/)
3. 从2000年的选举开始,新闻媒体在地图上开始用蓝色代表民主党,红色代表共和党。
4. gregor aisch, adampearce and karen yourish, “how large is the divide between red and blueameric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6
5. nelson schwartz andquoctrung bui, “where jobs are squeezed by chinese trade, voters seekextremes,”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2016
翻译:孙旖宁,
喧闹纷争的美国大选季即将结束,但是2016年大选的影响将长期存在。美国政治的观察家们担心此次大选反映的美国选民在政见上的分歧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都无法愈合。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2016大选是否会产生政党重新洗牌或者政党重组 (party realignment),从而长期改变美国两大政党的选民基础,使得极端意识形态回归到常规政治。
“政党重组”这个术语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v. o. key在1955年一篇文章中提出,是针对他所说的“关键选举”(critical elections)而言,这些选举“展现了现存选民分裂基础的巨大改变”[1]。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美国政治的周期循环:一段时期稳定的选举联盟(electoral coalition)。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一系列新议题的产生,大批选民的意愿发生改变。政党内部发生分歧。最终导致一场“关键选举”,拉开一段新的政治稳定时期的帷幕。总体上来说,美国两党体制趋向保守,所以很多政治学者认为,在常态政治和关键或重组选举之间的混乱与骚动,正是这种保守体制对人们在变革时代的政治诉求的应答。
每一次选举或政党重组一般会产生长达30-40年的改变。在美国历史上,政治学者至少发现了六次政党重组,最近发生的一次是在1980年代初,即所谓的“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问题是,2016年大选之后,美国会经历第七次政党重组吗?
不同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美国不会迎来第七次政党重组,因为在推动两大党对立的核心问题上,诸如种族、性别、福利、税收政策,两党的基本面立场并没有改变。我们再看一下美国选区地图,红蓝相间的版图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持着原先的模样。因此,在julia azari看来,2016大选至多“重新校准一些新议题受到关注后的政治方向,但是两大政党的选民阵营基本不受影响”[2]。
而很多别的学者不同意她的看法。他们预测美国政治将面临一系列基本层面的改变。我们可以说,美国社会在可以遇见的将来将进入一个“非常规政治”期(abnormal politics)。非常规政治的一大特征就是极端的党派性偏见(partisanship)和不稳定的选民联盟。在非常规政治时期,旧有的左派、右派或自由、保守的标签已经不再能够描述两党的派系差别。相反,我们发现右翼政客正在动员传统上是民主党稳定票仓的工人阶层,而民主党的政客则进入深红地带[3],企图策反主流保守派选民。政客之间激烈竞争,把温和中间派的选民推向两极,对大家熟悉的所谓“中间选民理论”(the medium voter thesis)构成挑战。中间选民理论认为,政客们一般都会向中间靠拢,选择温和将极力拉拢中间派,因为选民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呈正态分布。2016年的选举并非如此,特朗普不遗余力地动员共和党的右翼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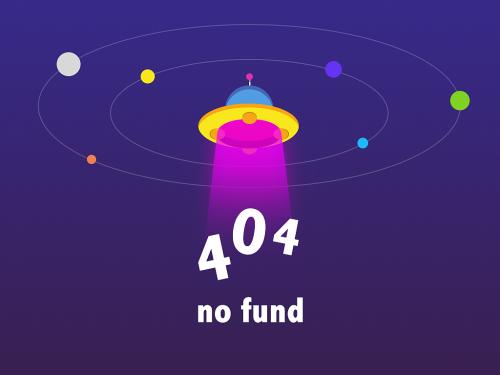
(商界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都站到希拉里一边)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2016年的非常规政治是美国选举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预兆。从民主党方面看,蓝领白人持续不断地流向共和党阵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特朗普的反贸易和反移民政策所诱惑。从共和党方面看,许多比较自由派的利商主义者都被特朗普的粗鄙而吓退,大量传统的共和党成员,包括商界精英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都站到希拉里一边。过一段时间,两党内部的震荡和混乱也许会平息下去,但在此同时,它可能会导致选民基本面的改变,久而久之,这种基本面的变化会改变两党所代表的利益结构。
单从白人选民在两党之间互换这件事,我们也许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些变化在数目上会有利于哪个党派?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变化可以改变两个政党的特性。试想一个萎缩着的工人阶层,现在因为种族的原因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种族身份认同就会作为一项政治诉求走向台前,而不是经济利益。2016年,低教育的白人工人没有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投票。相反的,因为特朗普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白人利益和身份的保护者,他们就将自己的命运与特朗普拴在一起,以期通过他来对抗移民、少数族裔和外国劳工。而对于民主党来说,受到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界精英大量涌入,必定会使其右倾,从一个倾向劳工阶层的政党转向为在经济社会政策上更加中性的政党。
那这次的选民重新站队会不会是一时一地的短暂现象?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特朗普吗?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美国社会在人口、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变化标志着未来的两党政治将面临重新洗牌。
首先,美国人口结构改变的趋势将有利于民主党,但是也意味着族群政治危机的加剧。许多研究表明美国选民中种族构成从1988年开始就朝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到2016年,非裔、西班牙裔、亚裔已经占总选民人数的31%。加上女性、拥有高等学历的白人和年轻选民,民主党将在未来几年内有效地扩大其选民基础。这个趋势早在特朗普涉足政坛前就已经出现,特朗普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攻击则加速了共和党选民的大批离去。与此同时,由于共和党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它将为美国的一部分白人本土主义者 (nativists)提供舞台,宣泄其对外国移民、少数族裔甚至建制派精英(establishment)的不满和抵制。
其次,美国乡村与城市、沿海与内陆、小城镇与大都市等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差距在过去20年间持续拉大。倾向于自由的地区越发自由,而倾向于保守的地区则越发保守,美国越来越多的郡县持续由一个政党占据绝对优势。这些郡县可以被称作是选票“悬殊郡县”(landslide counties),也就是说,在这些郡县,要么民主党,要么共和党通常会获得20%以上的压倒性胜利,而不是票数接近。据纽约时报,美国居住在“悬殊郡县”的选民数量从1992年的38%增加到2012年最近一次总统大选中的50%[4]。与此同时,一个日益清晰的两党选票版图正在形成,来自乡村、小镇和所谓“旧经济”地区的选民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而那些来自人口稠密、文化多元的都市选民更偏向于支持民主党。随着两党的分野在地理上变得格外清晰,民主党地区变得更蓝,共和党地区变得更红,美国两党对立的极化政治有了区域化的基础。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的政治分歧的强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的美国大选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也是影响未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性可以和英国脱欧相比。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谁得益、谁受损,从来就是个政治问题。但是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到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其中的因果关联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经济学家gordon hanso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那些受到贸易负面影响的地区更倾向于投票给思想极端的政客[5]。所以,特朗普作为政客不是特例,他不过是在迎合经济民粹主义者反贸易、反移民的诉求。
上述分析表明,因为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2016年美国大选所展露的非常态政治极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对美国政治体制将是一个考验。即便2016年本身不会成为政党重组的关键选举年,两党选民的互换,尤其是共和党内部的混乱,表明我们也许会看到又一轮的美国政党重新洗牌。
注释:
1. v. o. key,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thejournal of politics, 1955, vol. 17, no. 1, p. 4.
2. julia azari, “trump may bring a republicanrecalibration, not a realignment” (retrieved on october 30, 2016: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rump-may-bring-a-republican-recalibration-not-a-realignment/)
3. 从2000年的选举开始,新闻媒体在地图上开始用蓝色代表民主党,红色代表共和党。
4. gregor aisch, adampearce and karen yourish, “how large is the divide between red and blueameric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6
5. nelson schwartz andquoctrung bui, “where jobs are squeezed by chinese trade, voters seekextremes,”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2016
翻译:孙旖宁,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