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作者:埃里克·s·埃德尔曼(eric s. edelman)、雷·塔伊(ray takeyh);
政权更迭对华盛顿而言是一个“有毒”的词汇。它唤起了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印象,那时,美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泥潭当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拥护对伊强硬政策者常被指控秘密支持政权更迭的原因。对此,被指控者一直予以否认。他们不希望伊朗的政权更迭,并坚称只是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职人员改变他们的行为。
但这样的改变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伊朗政权中有绝不容纳美国的革命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政权更迭政策并非激进、鲁莽的想法,相反的,这是美国对伊朗政策中最务实、有效的目标。实际上,这是唯一有可能、有意义的减少伊朗威胁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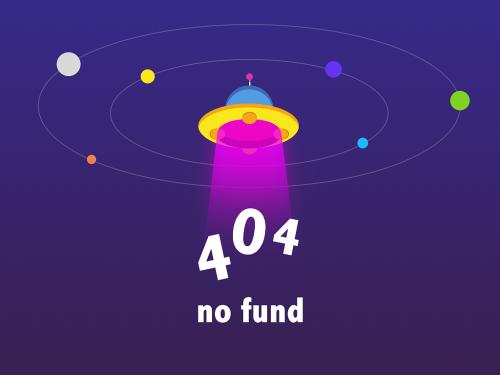
伊朗民众进行抗议,图片来源:reuters
支持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主张对伊朗进行军事入侵,但确实意味着美国要使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伊朗的宗教状态,其中包括秘密援助不同政见者。美国不可能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但可以为它的灭亡成为可能提供条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比许多西方分析人士认为的要弱,外界压力和内部抵抗运动都可能推翻它。近年来,公众对该政权广泛的反对声浪不断。伊朗人民渴望更好的领导,华盛顿的问题不应该是“是否接受政权更迭政策”,而是“如何帮助伊朗人民实现政权更迭”。 我们从未在一起
在过去40年里,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试图与伊朗达成某种协议。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计划导致他爆发了任期内最大的丑闻。他在黎巴嫩用武器装备交换民兵真主党所劫持的美国人,该党正是由伊朗支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试图与德黑兰制定缓和路线图,但没有成功。小布什(bush junior)上台后,在道德上对神权专制表达蔑视,但其政府却花费大量时间与伊朗领导人讨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未来。然后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不顾一切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给予伊朗制裁减免,为伊朗制造原子弹铺平了道路。
2018年,特朗普代表美国退出该协议,并对伊朗实施了比以往都严重的制裁。特朗普一再谴责该政策,今年年初,他下令杀害著名的圣城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下属单位)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但是,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表面上进行了对抗,其内在逻辑仍然与上任政府相似:对伊朗施加制裁,以便在谈判中获得影响力。特朗普仍然想要达成协议,事实上,他是第一个提议与伊朗领导人会晤的美国总统。
美国历任政府都不明白,伊朗政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革命组织。一旦掌权,革命者往往会屈服于温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诱惑。管理政府的务实主义,解决国内问题的要求,这些都会使政权适应当前的国际秩序。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诞生40年后,仍然逃避这种规律。伊朗政权的精英们即使被证明是弄巧成拙,也仍然坚持革命的戒律。这是因为革命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并不依赖世俗原则,而是将宗教作为执政信条。霍梅尼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一个政治化和激进化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基础上;一个在长期以来,与信仰传统相背的教派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伊朗最忠实的支持者来说,伊朗的神权统治仍然是理解真主旨意的重要方式。在霍梅尼的继任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领导下,这些信徒仍然控制着伊朗政府中最强大的分支,并成功的抵制了来自其他领导人和议会所作出的改革努力。
对于霍梅尼和他的门徒来说,革命不断的生命力迫使他们将其“出口”他国。这将是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他的吸引力不受穆斯林世界不同文化或不同民族感情的限制。哈梅内伊忠实地履行着这一使命,它在中东地区支持武装民兵,目的是为了推进伊朗式伊斯兰主义,破坏美国支持的地区安全秩序。在毛拉们偏爱的叙述中,美国帝国主义的角色一直试图利用该地区资源来扩张西方的工业化。
要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必须支持腐败的阿拉伯君主国和非法建立的犹太国家,从而征服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朗政权已经将抵制美国统治视作神圣的命令。
也正因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它绝不会允许真正的政治论战或有组织的反对派形成。为了商业发展,伊朗也绝不会放弃其核野心。它永远不会承认美国在中东的任何利益是合法的。革命者们永远不会放弃革命。 “活在当下”
由于无法与伊朗政权达成可持续的和解,美国唯一有意义的政策就是寻求政权更迭,也就是说,要尽一切可能削弱伊朗政府,并加强伊朗国内反政府者的声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多数的伊朗人,他们希望1979年那场推翻国王的革命的最初承诺能够兑现。那场革命得到了包括自由派和亲民主派在内的广泛团体的支持,但最后却被霍梅尼和他的伊斯兰主义团体劫持。美国应该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谦虚,并认识到自己并不总是可以制造事端。但考虑到神权政治的国家内部脆弱性,华盛顿仍然可以在削弱伊朗政权权利方面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美国不能精准的预测伊朗政府将如何垮台,也无法对谁会接手伊朗有确切的认知。但它可以对两件事造成极大影响。
今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陷入了僵局。该政权不得不面临不满的群众,他们正在失去恐惧感,开始愿意在街头对抗政府的安全部门。没有人知道神权时代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愿意去自己寻找。尽管革命具有“不妥协”的精神,但革命后的伊朗也并非没有改革者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由政治家、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试图调和信仰与自由。改革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严格定义将威胁到整个国家系统,因此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契约,维护伊朗的伊斯兰传统,并维护民主价值观。改革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席卷了政府和议会,但遭到哈梅内伊和强硬派们的阻挠。然而,那个时代勇敢的运动领袖,比如阿卜杜拉·努里(abdollah noori)、穆斯塔法·塔扎德 (mostafa tajzadeh)、赛义德·哈贾里安(saeed hajjarian),他们继续在伊朗内部为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斗争。
在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期间,人们表达了强硬的观点。在这次运动中,伊朗人举行示威,支持当年竞选总统的改革派人物,要求实行善政,并恢复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当政权为了确保保守派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oud ahmadinejad)获胜而操纵选举结果被揭露后,该运动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并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空前数量的民众走向街头,使得伊朗政府不得不诉诸武力以重获控制权。十多年后的今天,反对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 (mir-hossein mousavi)和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迈赫迪·卡鲁比 (mehdi karroubi)仍处于软禁当中。
绿色革命可能已经成为西方评论家们遥远的记忆,但它却一直困扰着伊朗政权。在镇压绿色革命几个月后的一次演讲中,时任革命卫队首领穆罕默德沙·阿里·贾法里 (mohammad ali jafari)承认,抗议活动使这个政权陷入了“被推翻的边缘”。2013年,哈梅内伊对一群学生说,绿色革命带了了“巨大的挑战”,并把政府带到了“悬崖边缘”。在这次改革之后,伊朗决定不再容忍国内的改革派。伊朗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自我毁灭中,清洗了该国许多知名的改革派人士。
在过去的两年里,伊朗发生了1979年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示威活动,甚至超过绿色革命。与早期大规模抗议运动相比,今天的抗议活动对神权政体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它们代表着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反抗,这些人是近年来示威者里的大多数。在早期的抗议活动中,政府对大学生和中产阶级抗议者并不重视,穆拉认为前者是富裕阶层被宠坏的后代,而后者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反对,不如说是对物质享受的渴望。但教权将穷人看作是政权的支柱,通过他们的虔诚与庇护将神权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伊朗的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飞涨。在2018年美国恢复制裁之前,伊朗石油日出口量为250万桶,现在已经降低到24.8万桶。这迫使国家削减了燃料补贴,石油收入的损失使得国家难以履行其养老金义务,也难以维持国家的房价在可负担的区间。让腐败的穆拉在福利国家的压力下做出牺牲的呼吁非常空洞。在去年的抗议活动中,人们高呼“把钱还给我们!资本家教士们!”(clerics with capital, give us our money back!)
但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示威者已经超越了以前仅仅对经济的不满,他们已经接受了政治性的口号,这震惊了伊朗政权。例如,2017年12月,基本商品价格飙升后,抗议浪潮席卷伊朗。主要城市的游行者公开高呼“哈梅内伊去死!”和“教士们应该迷路了。”当政府开始派出安全部队的武装力量后,示威活动逐渐消失。但去年11月,燃油价格忽然上涨,引起了数百个城市的骚乱,大约1500人死于警察和安全部队之手。这一次,示威者不仅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去死,他们还谴责伊朗参与其他地区的冲突。(“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想想我们吧,离开叙利亚!)即便伊朗政权谴责美帝国主义,其领导人却也在运用帝国主义的政策去让伊朗政权更加辉煌。但许多伊朗人似乎已经不想在阿拉伯内战中再浪费他们的资源。
今年1月,苏莱曼尼死于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之后,大批哀悼者涌向伊朗各个城市的街道,许多人认为这次袭击团结了伊朗人民支持他们的政权。然而就在几周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打破了团结的幻想。在几天的官方否认之后,伊朗政府最终承认,由于伊朗防空系统对美国入侵保持高度警惕,意外地击落了一架从德黑兰起飞的乌克兰民用客机,造成176人死亡。
伊朗政府与美国的新一轮对抗非但没有恢复毛拉们的优势,反而提醒了伊朗人民他们政府好战的代价。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伊朗政府的合法性再次受到了打击。在疫情期间,伊朗不仅未能保护其公民的健康和安全,而且由于隐瞒信息和问题阻碍了民众的自我保护。这导致该政权的信誉被进一步打击,并加剧民众多年以来积攒的愤怒。 我该如何帮助你?
虽然伊朗内部充满异议,但并没有出现一致的抵抗运动。华盛顿不能亲手创造这样一个运动,但可以通过削弱伊朗政权,暗中协助伊朗内部势力,激发民众对变革的需求。美国可以帮助目前相互脱节的反对派巩固势力,华盛顿也应该进一步消耗伊朗的经济,从伊朗政权执行者的军队中招兵买马,并暗中使用那些敢于挑战政权的人。但,美国不能更进一步,也就是推翻和取代神权体制,这必须由伊朗人自己承担。
落实政权更迭的目标花费并不巨大,但需要一个机密的行动计划,以此帮助伊朗民间社会中那些质疑政权合法性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专业集团,比如工会组织和教师联盟,他们会举行罢工,以此反对政府的政策与行动。除此之外还有学生团体,他们可以在大学校园内组织抗议活动。被肃清的改革派可以在公开信中抗议政府的虐待行为,并在示威活动被镇压后持续行动。
去年11月,绿色革命的领导人穆萨维在网站kaleme.com上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将政府的行为比作1978年9月沙阿军队的卑鄙屠杀。同样在11月,改革派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在instagram上谴责了这次镇压,称“任何政府在面对抗议时都无权诉诸武力和压迫。”
这些强有力的信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并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但是很难估计有多少伊朗人知道这些,因为政府干预并封锁了互联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必须向伊朗政权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提供技术和软件,以便他们可以躲避审查,相互沟通,美国也可以以此获得信息。
这种秘密的技术援助至关重要,但这并非华盛顿能够帮助培养反对派的唯一方式。直接(但秘密)的财政支持也必须发挥作用。伊朗工会应该是美国努力的重点,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石油和运输工人的罢工对伊朗政权的瘫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钢铁工人、卡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铁路工人、教师和甘蔗工人都呼吁罢工,以挑战现行制度。通过向可能实施类似运动组织提供资金,美国可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经济。
除了采取这种秘密措施外,华盛顿还应该调整和伊朗有关的公共外交。美国官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伊朗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警告说,如果伊朗有了新秩序,国际社会将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同时,华盛顿应该强调,伊朗政权中任何想要叛逃的成员都将在美国得到庇护。中央情报局应该建立一个机制来接触并接纳所有想要离开伊朗的人。即便是少数叛逃者也可能在系统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迫使安全部门不断在其内部寻找不可靠的分子,并定期进行清洗。通过在国家镇压机器中制造不信任和怀疑,以及消除伊朗内部一些骨干力量的方式,美国可以有效的妨碍伊朗政府的执政效率。
除了具体政策和官方言论以外,美国也必须通过向伊朗人民提供准确的资讯,可靠的分析来攻克政府的宣传。华盛顿每年花费3000万美元运营由美国全球媒体(global media)代理的波斯语媒体平台,其中包括法尔达电台(radio farda)和sedaye america,它们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提供新闻与娱乐节目。
根据该代理机构提供的消息,这一媒体方案覆盖了近四分之一的伊朗成年人。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公开资助流亡在美国的伊朗人,并制作广播和电视节目,从而加强宣传。虽然传统媒体形式很重要,但美国政府也可以使用instagram、telegram、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突出曝光具体的贪污案例,并点名对其负责的政府内部人员,从而引起人们对政权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善的更多关注。 压力之下
然而,援助伊朗境内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战斗的一半。为了削弱伊朗政权对伊朗的控制,并为其他力量掌权创造机会,美国必须扩大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经济实施的“极限施压”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立即驳斥了该计划,坚称单边制裁不会对伊朗的财政造成过大的压力。但他们高估了外国公司愿意冒险与美国周旋的意愿,虽然它们本国的政府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但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和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却已经离开了伊朗,以便逃离华盛顿的制裁。
美国还必须让伊朗在地区间的军事冒险主义付出更大的代价,对苏莱曼尼的袭击并非仅仅针对他个人,而是直接向伊朗“讨债”的第一步。伊朗的的干预已经使得其代理人所在的地区变得脆弱。
最近几个月,伊拉克大量民众走向街头,抗议德黑兰过度的影响力。而最近在黎巴嫩的抗议活动,也是由民众对伊朗长期影响的愤怒导致,许多黎巴嫩人开始对伊朗支持的民兵和政治组织真主党感到厌烦。华盛顿应该利用德黑兰在这些地区的失败作为财富,帮助对抗伊朗的团体,包括酌情通过秘密手段提供财政支持,并利用海军和航空资本组织伊朗的军需流向政权的代理人。
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的必要性也应该运用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地位上。美国应该在叙利亚维持少量的军事资产,以观察并阻挠伊朗将叙利亚领土转变为其代理人提供物资的“陆桥”。 批评者忽视了什么?
许多人反对政权更迭的议程。其一,美国对民主力量、人权活动家和伊朗政权批评者的援助会使他们在伊朗人的眼中蒙羞。但伊朗不同政见者本身无疑是这种风险的最佳判断者,华盛顿应该确定最有希望接受美国援助的人,并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过去十年内所经历的抗议活动中,美国从未受到谴责。事实上,在2009年,许多绿色革命的示威者呼吁奥巴马公开对其表示支持,但并没有成功。甚至去年,特朗普也没有成为伊朗抗议活动谴责的对象。抗议活动中流传最广的视频显示,游行的队伍刻意避开了伊朗当局涂在地上的美国国旗,当局则以这种手段迫使人们踩踏美国国旗来表示敌意。
其他对政权更迭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提及《阿尔及尔协定》,该协定结束了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危机,要求是华盛顿不能再干涉德黑兰内政。美国应该公开表示自己不再受协议的约束,因为该协议是在协迫下谈判的。伊朗绑架和杀害美国官员,协助袭击美国军事力量并支持恐怖主义团体,多次严重违反了该协议。
一些批评人士表示,公开推行政权更迭会使通过谈判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破灭。这一论断前提是与现行制度达成一项可靠的军备控制协定,但并没有。伊朗、美国与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存在致命缺陷,它没有禁止伊朗国内铀浓缩技术和先进离心机技术的发展,这让其他所有重要条款都丧失了意义。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以军备控制作为方法的外交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如此,为了保持国家间压力和国会对侵略性政策的支持,美国应该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即便在讲政权更迭做为目标后也应如此。伊朗人可能认为与鹰派政府谈判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说服政府放弃将政权更迭转变为一个具体目标。另一个反对政权更迭战略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神权政府都是很糟糕的。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成功的政权更迭不过是让一个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在革命卫队中崛起罢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从好战的神权国家变成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国家。但这是错误的假定,因为革命卫队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独立于教权领导的身份。在现实中,教权寡头和革命卫队的领袖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只是面对相同困境的不同侧面,穆拉对于年轻人不重视他们的革命规劝而感到痛苦;革命卫队则面临另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需要将从下层阶级招募来的新兵派到他们曾经居住的社区,去殴打并射杀他们的反对派同辈。
最后,对政权更迭持批评态度的人会警告说,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倒台。伊朗将像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或者2011年美国领导干预利比亚之后几年那样,成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但伊朗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异,伊朗的国家与政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与伊拉克和利比亚不同,伊朗并不是欧洲后殖民时代边界划分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尽管伊朗确实存在种族冲突,德黑兰的统治力量也确实压制了宗教少数派,但伊朗社会绝大多数是什叶派,没有令伊拉克或利比亚难以治理的部落派别和种族、宗教分裂。最后一点,即便伊朗处于神权统治下,其公民社会依旧繁荣。它并没有像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因为独裁者的长期统治而原子化。
当然,这些特点并不能保证伊朗会发展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神权政体倒台,就不可能准确的预测革命中会发生什么,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警示。但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相比,伊朗政治充满了活力,公民社会信息灵通,新闻界、知识界活跃,中产阶级人数众多,文化水平较高。
事实上,伊朗自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就是人们在拥有特权的君主和毛拉之间寻求自由的长期斗争的故事。1905年,伊朗立宪革命建立了该国的第一个议会,在随后的几年里,精力充沛的议员们大胆地对君主进行了限制。礼萨-沙阿·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在1925年上台后挑战了这一体系,将自己的意志暂时强加于国家。但他在1941年退位后,伊朗回到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道路上,总理与议会再次成为国家的重要角色。1953年,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总理通过将石油工业国有化引发了一场危机。令他下台的政变通常被视为英美阻止伊朗自治的阴谋。事实上,摩萨台也在试图用自己的独裁方式破坏民主发展,而他的倒台也主要是伊朗的倡议。接着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二十余年的独裁统治,他最终在1979年的民粹主义革命运动中被推翻,该运动包含许多联盟,目的是建立一个对伊朗传统积极而敏感的政府。
现在轮到穆拉们了,在其存在的每十年中,神权都面临着一场叛乱。上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者们首先反对穆拉间的权力争夺。在伊朗,大学生一直是政治先锋,1999年,他们抗议放弃神权政治,10年后,又一波青年叛乱袭击了该政权。在过去几年里,伊朗人又一次回击了,学生、工人、神职人员和商人都在支持反对专制统治,就像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今天在街上抗议的人将是明天领导伊朗的人,他们的斗争值得华盛顿的拥抱。 改变即将到来
伊朗人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并非与其领导人共同敌视西方。但是事情并不总是顺遂人意,为了避免伊朗产生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的结果,美国的政权更迭计划必须包括将神权时代的伊朗引向正确方向,美国对其结果负有很大的责任。一旦伊朗政权崩溃,美国必须立即取消所有制裁,并建立国际捐助关系,向伊朗注入资金,将其石油带回市场中。
即使美国帮助伊朗摆脱了旧的政权,华盛顿也必须对伊朗的国家复兴作出长期承诺,这样才能对其产生巨大影响。美国进行财政援助来稳定伊朗经济,并为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援助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和国会领导人必须向美国公众表明,这种援助对地区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华盛顿必须向伊朗的新统治者表明,任何援助都取决于其是否完全放弃了伊朗核武器计划。
对于任何新的领导人来说,治理伊朗都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在政权崩溃后不免会有清洗运动,但华盛顿必须向新的统治者施压,给那些希望成为新秩序一部分的老精英们留有空间。伊朗的核计划将会留下危险的余屑,理想状况下,应该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牵头,对伊朗的核技术和浓缩铀技术负责。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军方需使用联合军事行动,消除计划中的敏感部分,以防其落入危险者手中。
伊朗的政权更迭不会“好看”,也不会立即解决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稳定中东。但美国至少应该尝试赋予伊朗人民权力,让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政府。否则,华盛顿必定重蹈覆辙——假装有可能与穆拉谈判,盲目的期待神权革命的行动会产生“温和派”,让他们将政权从激进里引开;或者天真地希望民众的反抗在没有外界的支持下成功。这种方法已经失败了40多年,是时候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作者:埃里克·s·埃德尔曼(eric s. edelman)、雷·塔伊(ray takeyh);
政权更迭对华盛顿而言是一个“有毒”的词汇。它唤起了人们对伊拉克战争的印象,那时,美国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泥潭当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拥护对伊强硬政策者常被指控秘密支持政权更迭的原因。对此,被指控者一直予以否认。他们不希望伊朗的政权更迭,并坚称只是希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职人员改变他们的行为。
但这样的改变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伊朗政权中有绝不容纳美国的革命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政权更迭政策并非激进、鲁莽的想法,相反的,这是美国对伊朗政策中最务实、有效的目标。实际上,这是唯一有可能、有意义的减少伊朗威胁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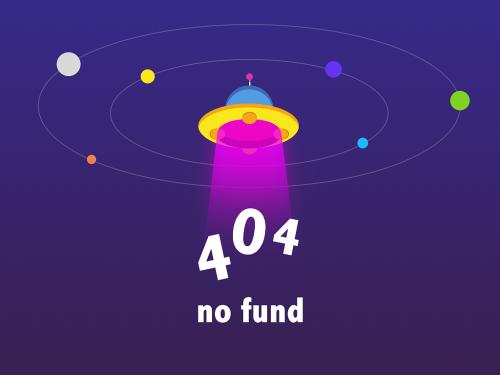
伊朗民众进行抗议,图片来源:reuters
支持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主张对伊朗进行军事入侵,但确实意味着美国要使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伊朗的宗教状态,其中包括秘密援助不同政见者。美国不可能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但可以为它的灭亡成为可能提供条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比许多西方分析人士认为的要弱,外界压力和内部抵抗运动都可能推翻它。近年来,公众对该政权广泛的反对声浪不断。伊朗人民渴望更好的领导,华盛顿的问题不应该是“是否接受政权更迭政策”,而是“如何帮助伊朗人民实现政权更迭”。 我们从未在一起
在过去40年里,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试图与伊朗达成某种协议。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计划导致他爆发了任期内最大的丑闻。他在黎巴嫩用武器装备交换民兵真主党所劫持的美国人,该党正是由伊朗支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试图与德黑兰制定缓和路线图,但没有成功。小布什(bush junior)上台后,在道德上对神权专制表达蔑视,但其政府却花费大量时间与伊朗领导人讨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未来。然后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不顾一切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给予伊朗制裁减免,为伊朗制造原子弹铺平了道路。
2018年,特朗普代表美国退出该协议,并对伊朗实施了比以往都严重的制裁。特朗普一再谴责该政策,今年年初,他下令杀害著名的圣城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下属单位)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但是,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表面上进行了对抗,其内在逻辑仍然与上任政府相似:对伊朗施加制裁,以便在谈判中获得影响力。特朗普仍然想要达成协议,事实上,他是第一个提议与伊朗领导人会晤的美国总统。
美国历任政府都不明白,伊朗政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革命组织。一旦掌权,革命者往往会屈服于温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诱惑。管理政府的务实主义,解决国内问题的要求,这些都会使政权适应当前的国际秩序。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诞生40年后,仍然逃避这种规律。伊朗政权的精英们即使被证明是弄巧成拙,也仍然坚持革命的戒律。这是因为革命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并不依赖世俗原则,而是将宗教作为执政信条。霍梅尼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一个政治化和激进化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基础上;一个在长期以来,与信仰传统相背的教派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伊朗最忠实的支持者来说,伊朗的神权统治仍然是理解真主旨意的重要方式。在霍梅尼的继任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领导下,这些信徒仍然控制着伊朗政府中最强大的分支,并成功的抵制了来自其他领导人和议会所作出的改革努力。
对于霍梅尼和他的门徒来说,革命不断的生命力迫使他们将其“出口”他国。这将是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他的吸引力不受穆斯林世界不同文化或不同民族感情的限制。哈梅内伊忠实地履行着这一使命,它在中东地区支持武装民兵,目的是为了推进伊朗式伊斯兰主义,破坏美国支持的地区安全秩序。在毛拉们偏爱的叙述中,美国帝国主义的角色一直试图利用该地区资源来扩张西方的工业化。
要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必须支持腐败的阿拉伯君主国和非法建立的犹太国家,从而征服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朗政权已经将抵制美国统治视作神圣的命令。
也正因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它绝不会允许真正的政治论战或有组织的反对派形成。为了商业发展,伊朗也绝不会放弃其核野心。它永远不会承认美国在中东的任何利益是合法的。革命者们永远不会放弃革命。 “活在当下”
由于无法与伊朗政权达成可持续的和解,美国唯一有意义的政策就是寻求政权更迭,也就是说,要尽一切可能削弱伊朗政府,并加强伊朗国内反政府者的声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多数的伊朗人,他们希望1979年那场推翻国王的革命的最初承诺能够兑现。那场革命得到了包括自由派和亲民主派在内的广泛团体的支持,但最后却被霍梅尼和他的伊斯兰主义团体劫持。美国应该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谦虚,并认识到自己并不总是可以制造事端。但考虑到神权政治的国家内部脆弱性,华盛顿仍然可以在削弱伊朗政权权利方面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美国不能精准的预测伊朗政府将如何垮台,也无法对谁会接手伊朗有确切的认知。但它可以对两件事造成极大影响。
今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陷入了僵局。该政权不得不面临不满的群众,他们正在失去恐惧感,开始愿意在街头对抗政府的安全部门。没有人知道神权时代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愿意去自己寻找。尽管革命具有“不妥协”的精神,但革命后的伊朗也并非没有改革者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由政治家、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试图调和信仰与自由。改革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严格定义将威胁到整个国家系统,因此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国家契约,维护伊朗的伊斯兰传统,并维护民主价值观。改革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席卷了政府和议会,但遭到哈梅内伊和强硬派们的阻挠。然而,那个时代勇敢的运动领袖,比如阿卜杜拉·努里(abdollah noori)、穆斯塔法·塔扎德 (mostafa tajzadeh)、赛义德·哈贾里安(saeed hajjarian),他们继续在伊朗内部为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斗争。
在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期间,人们表达了强硬的观点。在这次运动中,伊朗人举行示威,支持当年竞选总统的改革派人物,要求实行善政,并恢复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当政权为了确保保守派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oud ahmadinejad)获胜而操纵选举结果被揭露后,该运动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并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空前数量的民众走向街头,使得伊朗政府不得不诉诸武力以重获控制权。十多年后的今天,反对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 (mir-hossein mousavi)和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迈赫迪·卡鲁比 (mehdi karroubi)仍处于软禁当中。
绿色革命可能已经成为西方评论家们遥远的记忆,但它却一直困扰着伊朗政权。在镇压绿色革命几个月后的一次演讲中,时任革命卫队首领穆罕默德沙·阿里·贾法里 (mohammad ali jafari)承认,抗议活动使这个政权陷入了“被推翻的边缘”。2013年,哈梅内伊对一群学生说,绿色革命带了了“巨大的挑战”,并把政府带到了“悬崖边缘”。在这次改革之后,伊朗决定不再容忍国内的改革派。伊朗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自我毁灭中,清洗了该国许多知名的改革派人士。
在过去的两年里,伊朗发生了1979年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示威活动,甚至超过绿色革命。与早期大规模抗议运动相比,今天的抗议活动对神权政体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它们代表着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反抗,这些人是近年来示威者里的大多数。在早期的抗议活动中,政府对大学生和中产阶级抗议者并不重视,穆拉认为前者是富裕阶层被宠坏的后代,而后者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反对,不如说是对物质享受的渴望。但教权将穷人看作是政权的支柱,通过他们的虔诚与庇护将神权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伊朗的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飞涨。在2018年美国恢复制裁之前,伊朗石油日出口量为250万桶,现在已经降低到24.8万桶。这迫使国家削减了燃料补贴,石油收入的损失使得国家难以履行其养老金义务,也难以维持国家的房价在可负担的区间。让腐败的穆拉在福利国家的压力下做出牺牲的呼吁非常空洞。在去年的抗议活动中,人们高呼“把钱还给我们!资本家教士们!”(clerics with capital, give us our money back!)
但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示威者已经超越了以前仅仅对经济的不满,他们已经接受了政治性的口号,这震惊了伊朗政权。例如,2017年12月,基本商品价格飙升后,抗议浪潮席卷伊朗。主要城市的游行者公开高呼“哈梅内伊去死!”和“教士们应该迷路了。”当政府开始派出安全部队的武装力量后,示威活动逐渐消失。但去年11月,燃油价格忽然上涨,引起了数百个城市的骚乱,大约1500人死于警察和安全部队之手。这一次,示威者不仅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去死,他们还谴责伊朗参与其他地区的冲突。(“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想想我们吧,离开叙利亚!)即便伊朗政权谴责美帝国主义,其领导人却也在运用帝国主义的政策去让伊朗政权更加辉煌。但许多伊朗人似乎已经不想在阿拉伯内战中再浪费他们的资源。
今年1月,苏莱曼尼死于美国的无人机袭击之后,大批哀悼者涌向伊朗各个城市的街道,许多人认为这次袭击团结了伊朗人民支持他们的政权。然而就在几周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打破了团结的幻想。在几天的官方否认之后,伊朗政府最终承认,由于伊朗防空系统对美国入侵保持高度警惕,意外地击落了一架从德黑兰起飞的乌克兰民用客机,造成176人死亡。
伊朗政府与美国的新一轮对抗非但没有恢复毛拉们的优势,反而提醒了伊朗人民他们政府好战的代价。
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伊朗政府的合法性再次受到了打击。在疫情期间,伊朗不仅未能保护其公民的健康和安全,而且由于隐瞒信息和问题阻碍了民众的自我保护。这导致该政权的信誉被进一步打击,并加剧民众多年以来积攒的愤怒。 我该如何帮助你?
虽然伊朗内部充满异议,但并没有出现一致的抵抗运动。华盛顿不能亲手创造这样一个运动,但可以通过削弱伊朗政权,暗中协助伊朗内部势力,激发民众对变革的需求。美国可以帮助目前相互脱节的反对派巩固势力,华盛顿也应该进一步消耗伊朗的经济,从伊朗政权执行者的军队中招兵买马,并暗中使用那些敢于挑战政权的人。但,美国不能更进一步,也就是推翻和取代神权体制,这必须由伊朗人自己承担。
落实政权更迭的目标花费并不巨大,但需要一个机密的行动计划,以此帮助伊朗民间社会中那些质疑政权合法性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专业集团,比如工会组织和教师联盟,他们会举行罢工,以此反对政府的政策与行动。除此之外还有学生团体,他们可以在大学校园内组织抗议活动。被肃清的改革派可以在公开信中抗议政府的虐待行为,并在示威活动被镇压后持续行动。
去年11月,绿色革命的领导人穆萨维在网站kaleme.com上发表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将政府的行为比作1978年9月沙阿军队的卑鄙屠杀。同样在11月,改革派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在instagram上谴责了这次镇压,称“任何政府在面对抗议时都无权诉诸武力和压迫。”
这些强有力的信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并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但是很难估计有多少伊朗人知道这些,因为政府干预并封锁了互联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必须向伊朗政权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提供技术和软件,以便他们可以躲避审查,相互沟通,美国也可以以此获得信息。
这种秘密的技术援助至关重要,但这并非华盛顿能够帮助培养反对派的唯一方式。直接(但秘密)的财政支持也必须发挥作用。伊朗工会应该是美国努力的重点,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石油和运输工人的罢工对伊朗政权的瘫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钢铁工人、卡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铁路工人、教师和甘蔗工人都呼吁罢工,以挑战现行制度。通过向可能实施类似运动组织提供资金,美国可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经济。
除了采取这种秘密措施外,华盛顿还应该调整和伊朗有关的公共外交。美国官员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伊朗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警告说,如果伊朗有了新秩序,国际社会将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同时,华盛顿应该强调,伊朗政权中任何想要叛逃的成员都将在美国得到庇护。中央情报局应该建立一个机制来接触并接纳所有想要离开伊朗的人。即便是少数叛逃者也可能在系统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迫使安全部门不断在其内部寻找不可靠的分子,并定期进行清洗。通过在国家镇压机器中制造不信任和怀疑,以及消除伊朗内部一些骨干力量的方式,美国可以有效的妨碍伊朗政府的执政效率。
除了具体政策和官方言论以外,美国也必须通过向伊朗人民提供准确的资讯,可靠的分析来攻克政府的宣传。华盛顿每年花费3000万美元运营由美国全球媒体(global media)代理的波斯语媒体平台,其中包括法尔达电台(radio farda)和sedaye america,它们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提供新闻与娱乐节目。
根据该代理机构提供的消息,这一媒体方案覆盖了近四分之一的伊朗成年人。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公开资助流亡在美国的伊朗人,并制作广播和电视节目,从而加强宣传。虽然传统媒体形式很重要,但美国政府也可以使用instagram、telegram、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突出曝光具体的贪污案例,并点名对其负责的政府内部人员,从而引起人们对政权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善的更多关注。 压力之下
然而,援助伊朗境内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战斗的一半。为了削弱伊朗政权对伊朗的控制,并为其他力量掌权创造机会,美国必须扩大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经济实施的“极限施压”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立即驳斥了该计划,坚称单边制裁不会对伊朗的财政造成过大的压力。但他们高估了外国公司愿意冒险与美国周旋的意愿,虽然它们本国的政府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但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和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却已经离开了伊朗,以便逃离华盛顿的制裁。
美国还必须让伊朗在地区间的军事冒险主义付出更大的代价,对苏莱曼尼的袭击并非仅仅针对他个人,而是直接向伊朗“讨债”的第一步。伊朗的的干预已经使得其代理人所在的地区变得脆弱。
最近几个月,伊拉克大量民众走向街头,抗议德黑兰过度的影响力。而最近在黎巴嫩的抗议活动,也是由民众对伊朗长期影响的愤怒导致,许多黎巴嫩人开始对伊朗支持的民兵和政治组织真主党感到厌烦。华盛顿应该利用德黑兰在这些地区的失败作为财富,帮助对抗伊朗的团体,包括酌情通过秘密手段提供财政支持,并利用海军和航空资本组织伊朗的军需流向政权的代理人。
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的必要性也应该运用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地位上。美国应该在叙利亚维持少量的军事资产,以观察并阻挠伊朗将叙利亚领土转变为其代理人提供物资的“陆桥”。 批评者忽视了什么?
许多人反对政权更迭的议程。其一,美国对民主力量、人权活动家和伊朗政权批评者的援助会使他们在伊朗人的眼中蒙羞。但伊朗不同政见者本身无疑是这种风险的最佳判断者,华盛顿应该确定最有希望接受美国援助的人,并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朗过去十年内所经历的抗议活动中,美国从未受到谴责。事实上,在2009年,许多绿色革命的示威者呼吁奥巴马公开对其表示支持,但并没有成功。甚至去年,特朗普也没有成为伊朗抗议活动谴责的对象。抗议活动中流传最广的视频显示,游行的队伍刻意避开了伊朗当局涂在地上的美国国旗,当局则以这种手段迫使人们踩踏美国国旗来表示敌意。
其他对政权更迭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提及《阿尔及尔协定》,该协定结束了1979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危机,要求是华盛顿不能再干涉德黑兰内政。美国应该公开表示自己不再受协议的约束,因为该协议是在协迫下谈判的。伊朗绑架和杀害美国官员,协助袭击美国军事力量并支持恐怖主义团体,多次严重违反了该协议。
一些批评人士表示,公开推行政权更迭会使通过谈判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破灭。这一论断前提是与现行制度达成一项可靠的军备控制协定,但并没有。伊朗、美国与其他大国达成的核协议存在致命缺陷,它没有禁止伊朗国内铀浓缩技术和先进离心机技术的发展,这让其他所有重要条款都丧失了意义。
事实上,美国和伊朗以军备控制作为方法的外交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尽管如此,为了保持国家间压力和国会对侵略性政策的支持,美国应该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即便在讲政权更迭做为目标后也应如此。伊朗人可能认为与鹰派政府谈判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说服政府放弃将政权更迭转变为一个具体目标。另一个反对政权更迭战略的原因是,任何一个神权政府都是很糟糕的。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成功的政权更迭不过是让一个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在革命卫队中崛起罢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从好战的神权国家变成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国家。但这是错误的假定,因为革命卫队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独立于教权领导的身份。在现实中,教权寡头和革命卫队的领袖是不可分割的。他们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只是面对相同困境的不同侧面,穆拉对于年轻人不重视他们的革命规劝而感到痛苦;革命卫队则面临另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需要将从下层阶级招募来的新兵派到他们曾经居住的社区,去殴打并射杀他们的反对派同辈。
最后,对政权更迭持批评态度的人会警告说,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倒台。伊朗将像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或者2011年美国领导干预利比亚之后几年那样,成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但伊朗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异,伊朗的国家与政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与伊拉克和利比亚不同,伊朗并不是欧洲后殖民时代边界划分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尽管伊朗确实存在种族冲突,德黑兰的统治力量也确实压制了宗教少数派,但伊朗社会绝大多数是什叶派,没有令伊拉克或利比亚难以治理的部落派别和种族、宗教分裂。最后一点,即便伊朗处于神权统治下,其公民社会依旧繁荣。它并没有像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因为独裁者的长期统治而原子化。
当然,这些特点并不能保证伊朗会发展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神权政体倒台,就不可能准确的预测革命中会发生什么,阿拉伯之春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警示。但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相比,伊朗政治充满了活力,公民社会信息灵通,新闻界、知识界活跃,中产阶级人数众多,文化水平较高。
事实上,伊朗自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就是人们在拥有特权的君主和毛拉之间寻求自由的长期斗争的故事。1905年,伊朗立宪革命建立了该国的第一个议会,在随后的几年里,精力充沛的议员们大胆地对君主进行了限制。礼萨-沙阿·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在1925年上台后挑战了这一体系,将自己的意志暂时强加于国家。但他在1941年退位后,伊朗回到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道路上,总理与议会再次成为国家的重要角色。1953年,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总理通过将石油工业国有化引发了一场危机。令他下台的政变通常被视为英美阻止伊朗自治的阴谋。事实上,摩萨台也在试图用自己的独裁方式破坏民主发展,而他的倒台也主要是伊朗的倡议。接着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二十余年的独裁统治,他最终在1979年的民粹主义革命运动中被推翻,该运动包含许多联盟,目的是建立一个对伊朗传统积极而敏感的政府。
现在轮到穆拉们了,在其存在的每十年中,神权都面临着一场叛乱。上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者们首先反对穆拉间的权力争夺。在伊朗,大学生一直是政治先锋,1999年,他们抗议放弃神权政治,10年后,又一波青年叛乱袭击了该政权。在过去几年里,伊朗人又一次回击了,学生、工人、神职人员和商人都在支持反对专制统治,就像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今天在街上抗议的人将是明天领导伊朗的人,他们的斗争值得华盛顿的拥抱。 改变即将到来
伊朗人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并非与其领导人共同敌视西方。但是事情并不总是顺遂人意,为了避免伊朗产生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的结果,美国的政权更迭计划必须包括将神权时代的伊朗引向正确方向,美国对其结果负有很大的责任。一旦伊朗政权崩溃,美国必须立即取消所有制裁,并建立国际捐助关系,向伊朗注入资金,将其石油带回市场中。
即使美国帮助伊朗摆脱了旧的政权,华盛顿也必须对伊朗的国家复兴作出长期承诺,这样才能对其产生巨大影响。美国进行财政援助来稳定伊朗经济,并为其他国家的进一步援助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和国会领导人必须向美国公众表明,这种援助对地区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华盛顿必须向伊朗的新统治者表明,任何援助都取决于其是否完全放弃了伊朗核武器计划。
对于任何新的领导人来说,治理伊朗都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在政权崩溃后不免会有清洗运动,但华盛顿必须向新的统治者施压,给那些希望成为新秩序一部分的老精英们留有空间。伊朗的核计划将会留下危险的余屑,理想状况下,应该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牵头,对伊朗的核技术和浓缩铀技术负责。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军方需使用联合军事行动,消除计划中的敏感部分,以防其落入危险者手中。
伊朗的政权更迭不会“好看”,也不会立即解决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稳定中东。但美国至少应该尝试赋予伊朗人民权力,让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政府。否则,华盛顿必定重蹈覆辙——假装有可能与穆拉谈判,盲目的期待神权革命的行动会产生“温和派”,让他们将政权从激进里引开;或者天真地希望民众的反抗在没有外界的支持下成功。这种方法已经失败了40多年,是时候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