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出版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畅想到了2033年,统治英国社会的阶层从贵族变成精英,整个社会奉行“智商 努力”的优绩主义信条。但是,这种优绩主义使得阶层分化过于严重,遭到民粹主义者反抗,社会濒临革命。
当时,对于杨来说,“优绩主义”(meritocracy,也可翻译为“贤能主义”或“精英主义”)是个贬义词。令他沮丧的是,后来“优绩主义”变成褒义词。从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到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都是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巴拉克·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的140多场演讲中,也像喊口号一样不断念叨着——“只要努力,你就能成功”。
过去半个世纪,在机会平等的外衣下,优绩主义成为英美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几乎可以被看作“美国梦”的内核。但是,自2016年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优绩主义遭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评。

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今年9月,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公共知识分子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出版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也可翻译为“贤能的暴政”或“精英的暴政”),加入了重估优绩主义的讨论。现年67岁的他,年轻时因批判大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而声名鹊起。后来,他渐渐成为哲学思想的普及者,阐明公民生活背后的诸多伦理难题,关心公民德性。其中,他最有名的是哲学公开课《公正》,被称作“全球摇滚巨星一样的哲学家”。
在新书中,桑德尔运用优绩主义解释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在反对移民、外包业务和低收入等方面外,更多的是抱怨“优绩的暴政”。在他看来,这种抱怨具有正当性。
“我对特朗普没有任何同情,他是个恶毒的人。但是,我的新书表达了对特朗普选民的同情。尽管特朗普说了万千谎言,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对精英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怨恨。他认为,精英阶层一辈子都看不起他。这的确为理解他的政治魅力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桑德尔对《卫报》说。
桑德尔在新书中称,美国民粹主义怨恨的核心是对工作的不满。这种不满,不只关于失业和工资停滞。“工作”,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文化意义。那些被全球化所抛弃的人们,不仅在别人发达时挣扎,也感觉自己的工作不再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得以养家糊口,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今天,这种情况要困难得多。过去40年,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翻了一番。
桑德尔觉得,近几十年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深化,毒害了政治环境,分裂了人群。这种鸿沟,一部分是由不平等所造成,但也和人们对于成败的态度有关。那些在顶层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这是一种衡量价值的方式,而那些失败者,不应归咎于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
这种对于成功的想法,来自一种看似吸引人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当然,在实际层面上,人们离这样的理想很遥远,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往上流动。出身贫穷家庭的孩童往往在长大后依然贫困,而富裕的父母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孩子。比方说,在常春藤联盟大学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人数,比来自金字塔后50%家庭的学生加总起来还多。
另一方面,桑德尔认为,全球化给优绩主义竞赛的获胜者带来丰厚回报。但是,这对大多数工人没有任何好处。生产率提高了,但劳动人民的所得越来越少。尽管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85%,但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现在的实际收入比当时要少。
不过,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们未能达到自己所宣称的优绩主义的平等原则,而是优绩主义这种理想本身存在缺陷。优绩主义会侵蚀公共利益,导致成功者傲慢,使失败者蒙羞。它鼓励成功者深信他们成功的事实,忘记帮助他们前进的运气,轻视那些运气和资格条件比他们差的人。
比如,持优绩主义立场的人可能会说,“如果你想在全球的经济中竞争并且获得胜利,那么就去念大学。”“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学习什么。”“如果你尝试,就可以成功。”
“这些精英忽略这些说法背后隐含的羞辱。如果你不去念大学,如果你没在这个新经济中发展,那么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其中的隐含之意。难怪许多劳动者反对优绩制下的精英。”桑德尔说。
而且,优绩主义给我们时代造成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伤害——侵蚀工作尊严。那些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继续上大学的人,贬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专业人士的工作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
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社会分化,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最终,优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起推动劳动人民对精英阶层的不满,并在政治层面引发相关的效应。
所以,桑德尔认为,民粹主义抱怨“优绩的暴政”是正当的。因为彻底的优绩主义不承认任何天赋或恩惠,它让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处于某种命运共同体中,也让我们在反思自己的才能和财富时无法产生团结感。这也是优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暴政的原因。
对于因优绩的暴政而遭受委屈的那些人来说,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更在于社会自尊的缺失。这时,他们的悲哀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不公正,而且是他们感到自己被羞辱。
据《金融时报》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在新书《死于绝望》(deaths of despair)中,详细阐述这种情况对工薪阶层白人男性所造成的伤害。轻蔑,和贫穷一样致命。在等级制度中处于低位,人们会产生压力和焦虑,引发破坏免疫系统的皮质醇在体内释放。借用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关于美国南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书名,一些白人工人阶级被剥夺受尊重感,与国家不断改变的文化格格不入,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因此,桑德尔觉得,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政治党派(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对优绩主义的追求,背叛了传统的工人阶级,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官僚治理方式,从而在竞选中失利。比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70%以上拥有高等学位的选民。
他认为,正是民主党对市场假设和优绩主义不加批判地拥抱,才为特朗普铺平道路。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拜登是36年来第一个没有常春藤大学学位的民主党候选人,这让他在美国大选中获得了某种优势。不过,即使特朗普大选落败,民主党未来也不一定会成功,除非他们重新定义使命,更加关注合理的不满和怨恨,而进步政治在全球化时代做出了贡献。
面对优绩的暴政,桑德尔希望所有公民思考:怎样才能促进人们的共同利益?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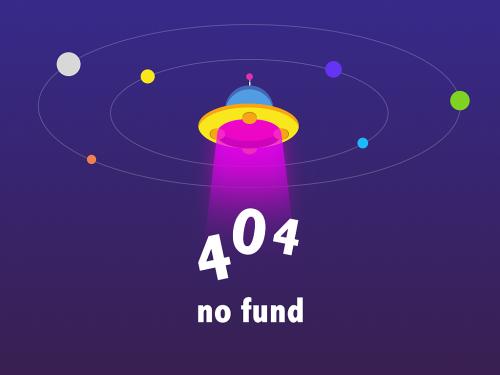
比如,他从大学角色、工作尊严、成功意义三个层面,提了一些建议。
在大学层面,桑德尔觉得,将大学所扮演的角色看成是机会仲裁者,这已经值得商榷了。事实上,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并没有大学学历。因此,创造一个经济体,让大学文凭被看作是获得具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想法相当愚蠢。
当然,他也承认,鼓励人们去念大学是件好事,但得为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提供更多机会。为了让美国人认识到择优录取的运气成分,他甚至提出一种看似激进的方案:所有学生达到给定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参加录取,并可给予额外抽签,以确保多样性。抽签,不仅会让寻求大学录取的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大学录取学生的傲慢。
在工作层面,桑德尔认为,人们应该重塑工作的尊严。工作不仅是在满足温饱,也是在促进公共利益,理应得到认可。
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看法——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标和终结。但是,桑德尔觉得,他们或许忘记古典道德和政治思想传统,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繁荣取决于培养和锻炼我们的能力来实现我们的本性;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教导说,职业培养公民自治的美德。
所以,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作为生产者,我们发展和运用自身能力提供满足同胞所需,赢得社会尊重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所做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用工资来衡量,而取决于努力所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方面的重要性。
为说明这一点,桑德尔打了个比方:想想沃尔特·怀特的两个职业,他是高中化学教师,在美剧《绝命毒师》中变成冰毒大亨。当怀特离开教室,将技能应用于制作冰毒时,挣的钱远远超过他做教师获得的微薄工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作冰毒比做高中老师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谁对共同利益的贡献最大,不能由市场决定,需要民主社会的公民辩论,达成共识,形成道德判断。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很可能改变许多美国人对谁的贡献最重要的感知。我们所依赖的是那些‘基本工人’,但他们是社会中收入最少的成员。”
为强调工作是使公民聚集在一个相互贡献和认可的网络,桑德尔又讲了一个故事。
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几个小时,回想起在田纳西州曼菲斯清洁工人所发起的罢工事件,说:“归根结底,捡垃圾的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他不工作,疾病就会蔓延。所有工作都有其尊严。”
桑德尔称,新冠疫情让这个道理更清楚。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劳动者,如送货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员工、仓库工人、货车司机、护理师助理、育儿员、居家照护业者……这些并不是薪资最好或最光荣的工作者。但现在,我们将他们视为不可或缺的工作者。这是一个开启公共辩论的时刻,讨论如何使他们的薪水,及其所获得的认同,能够与其工作重要性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重塑工作尊严可考虑两个方向的政策:一是对低收入工人的工资补贴,比如政府可根据目标小时工资,为低工资雇员每工作一小时提供一笔补充款;另一方法是降低甚至取消工资税,并通过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交易征税来增加收入。
不过,《华盛顿月刊》一篇评论批评桑德尔遗漏工会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工会的衰落远远超过其他面临类似全球化压力的国家。这种衰落是因为美国法律没有认识到组织劳工是一种公民权利。雇主经常因为员工组织工会解雇他们,但现在对这种手段的惩罚极弱。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国会应将1991年的《民权法》扩大到那些因试图建立工会而被解雇的人。”
最后,在成功意义层面,桑德尔觉得,人们可以扪心自问:“我在道德上应该得到使我蓬勃发展的才能吗?我的成就是否源自于我活在一个奖励才华的社会中,而这个才华是我正好所拥有的?还是只因为我很幸运而已?”
在他看来,坚信成功是因为自身的缘故,让人很难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困境。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会促使我们变得谦卑。或许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或者神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奥秘,所以“我”才能到达某个高度。
他举了个例子:现在人们喜欢篮球,所以,擅长精准投篮就具有极大的市场价值。这也是勒布朗·詹姆斯能赚那么多钱的原因。然而,他只不过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人们热爱篮球的时代。假设他生活在中世纪,具有同样的投篮天赋,但消费者市场完全不同,人们不关心他是否会投篮,而只关心他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战士或牧师,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富有。既然他生活在什么时代、消费者市场会怎样,都不取决于他本人的作为,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说,他应当获得他现在从市场中赚到的那些钱。
“这种谦卑的精神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公民素养。这个契机让我们可以从分裂彼此的成功道德观走回正轨,引领我们超越独裁的优绩体制,走向一个少点怨恨,更加慷慨的公共生活。”桑德尔说。
这几年,英语世界出现了很多批判优绩主义的作品,反思精英统治,这也是桑德尔新书诞生的背景。
它们多从教育角度切入,比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拉妮·吉尼尔(lani guinier)的《优绩制的暴政: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the tyranny of the meritocracy: democratiz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的《优绩制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过渡》(the crisis of the meritocracy: britain’s transition to mass education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how america'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等。
其中,去年出版的《优绩制的陷阱》受到许多关注和讨论。作者马科维茨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的主要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所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优绩制只是一个陷阱,滋养不平等,瓦解中产阶级,吞噬精英阶层。最终,它促使社会分裂,侵蚀民主政治,推动民粹主义兴起。
在另一个维度上,如果从桑德尔的内在思想脉络出发,《优绩的暴政》和他之前作品实则一脉相承。
在第一本书《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他反对康德式和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们虽然没有讨论技术官僚,但秉持的是正当应该优先于善的观念。而他所赞成的政治主张是善应该优先于正当,因此它必然涉及德性、道德品质和道德教育。
在后来的《民主的不满》中,桑德尔梳理美国的政治传统,试图表明美国国父们在建国之初曾非常热衷于培养公民德性。但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政治争论转向了康德和罗尔斯式的观念,德性的成分被排挤了。最近几十年,德性的成分消失,技术官僚和专家获得统治地位。
到了《金钱不能买什么》,他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市场和市场价值观逐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们的生活。但这存在问题,某些社会领域不应该由市场思维介入,人们需要认真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性,形成更健康的公共生活。
目睹这些年的政治变化,深感公民德性和共同利益讨论的缺失,他才写下《优绩的暴政》。
有意思的是,以批判罗尔斯成名的桑德尔,同意罗尔斯关于运气的观点:由竞争性市场所界定的经济回报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因此不能说,人们在道德上应当获得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所赚到的一切。
但是,他不同意罗尔斯认为分配正义和优绩无关,觉得在分配正义中可以有优绩,只要这种优绩是根据道德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根据市场的共同利益来界定。比如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多半会赞同,教师或医生在道德上应当比华尔街投机者们得到更多报酬。
“如果有人质问我:当人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究竟如何推理共同利益?对此,我的回应是:让我们一个个地来。我会问:如果说给赌徒提供赌场的那些人所具有的价值或道德重要性,比不上那些治病救人的医生或教书育人的教师,你们会同意吗?也许,我们在很多地方无法达成一致,但我们也会找到一些普遍的原则。在我看来,认为我们完全无法就‘什么是共同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达成一致,并且因此而拒绝任何尝试,这是错误的。”桑德尔说。
这也是桑德尔给我们的启示,你对他的观点同意与否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公共讨论和公民生活。唯在公共讨论中,哲学才最有价值。
“哲学并非大而抽象的问题,而是体现在我们不同的信仰和观点中。如果公众有机会这样坐下来讨论,彼此倾听观点背后的根源,而不是简单的投票,或许我们仍然会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但也有可能受到别人观点的启发而改变,这就是令人兴奋而极具挑战的哲学层面。当我们对曾经坚信的事情动摇的时候,说明我们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参考资料来自《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卫报》《哈佛杂志》《华盛顿月刊》《哲学动态》等。)
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出版反乌托邦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1870—2033》(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畅想到了2033年,统治英国社会的阶层从贵族变成精英,整个社会奉行“智商 努力”的优绩主义信条。但是,这种优绩主义使得阶层分化过于严重,遭到民粹主义者反抗,社会濒临革命。
当时,对于杨来说,“优绩主义”(meritocracy,也可翻译为“贤能主义”或“精英主义”)是个贬义词。令他沮丧的是,后来“优绩主义”变成褒义词。从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到比尔·克林顿、托尼·布莱尔,都是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巴拉克·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的140多场演讲中,也像喊口号一样不断念叨着——“只要努力,你就能成功”。
过去半个世纪,在机会平等的外衣下,优绩主义成为英美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几乎可以被看作“美国梦”的内核。但是,自2016年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优绩主义遭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评。

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今年9月,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公共知识分子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出版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也可翻译为“贤能的暴政”或“精英的暴政”),加入了重估优绩主义的讨论。现年67岁的他,年轻时因批判大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而声名鹊起。后来,他渐渐成为哲学思想的普及者,阐明公民生活背后的诸多伦理难题,关心公民德性。其中,他最有名的是哲学公开课《公正》,被称作“全球摇滚巨星一样的哲学家”。
在新书中,桑德尔运用优绩主义解释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在反对移民、外包业务和低收入等方面外,更多的是抱怨“优绩的暴政”。在他看来,这种抱怨具有正当性。
“我对特朗普没有任何同情,他是个恶毒的人。但是,我的新书表达了对特朗普选民的同情。尽管特朗普说了万千谎言,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他对精英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怨恨。他认为,精英阶层一辈子都看不起他。这的确为理解他的政治魅力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桑德尔对《卫报》说。
桑德尔在新书中称,美国民粹主义怨恨的核心是对工作的不满。这种不满,不只关于失业和工资停滞。“工作”,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文化意义。那些被全球化所抛弃的人们,不仅在别人发达时挣扎,也感觉自己的工作不再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
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有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得以养家糊口,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今天,这种情况要困难得多。过去40年,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翻了一番。
桑德尔觉得,近几十年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鸿沟深化,毒害了政治环境,分裂了人群。这种鸿沟,一部分是由不平等所造成,但也和人们对于成败的态度有关。那些在顶层的人,认为自己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这是一种衡量价值的方式,而那些失败者,不应归咎于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
这种对于成功的想法,来自一种看似吸引人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就是“优绩主义”的核心。当然,在实际层面上,人们离这样的理想很遥远,不是所有人都有平等机会往上流动。出身贫穷家庭的孩童往往在长大后依然贫困,而富裕的父母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孩子。比方说,在常春藤联盟大学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人数,比来自金字塔后50%家庭的学生加总起来还多。
另一方面,桑德尔认为,全球化给优绩主义竞赛的获胜者带来丰厚回报。但是,这对大多数工人没有任何好处。生产率提高了,但劳动人民的所得越来越少。尽管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85%,但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现在的实际收入比当时要少。
不过,问题不仅仅在于人们未能达到自己所宣称的优绩主义的平等原则,而是优绩主义这种理想本身存在缺陷。优绩主义会侵蚀公共利益,导致成功者傲慢,使失败者蒙羞。它鼓励成功者深信他们成功的事实,忘记帮助他们前进的运气,轻视那些运气和资格条件比他们差的人。
比如,持优绩主义立场的人可能会说,“如果你想在全球的经济中竞争并且获得胜利,那么就去念大学。”“你赚多少钱,取决于你学习什么。”“如果你尝试,就可以成功。”
“这些精英忽略这些说法背后隐含的羞辱。如果你不去念大学,如果你没在这个新经济中发展,那么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其中的隐含之意。难怪许多劳动者反对优绩制下的精英。”桑德尔说。
而且,优绩主义给我们时代造成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伤害——侵蚀工作尊严。那些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继续上大学的人,贬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专业人士的工作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更小。
这种思维方式造成社会分化,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最终,优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起推动劳动人民对精英阶层的不满,并在政治层面引发相关的效应。
所以,桑德尔认为,民粹主义抱怨“优绩的暴政”是正当的。因为彻底的优绩主义不承认任何天赋或恩惠,它让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处于某种命运共同体中,也让我们在反思自己的才能和财富时无法产生团结感。这也是优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暴政的原因。
对于因优绩的暴政而遭受委屈的那些人来说,问题不仅在于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更在于社会自尊的缺失。这时,他们的悲哀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不公正,而且是他们感到自己被羞辱。
据《金融时报》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在新书《死于绝望》(deaths of despair)中,详细阐述这种情况对工薪阶层白人男性所造成的伤害。轻蔑,和贫穷一样致命。在等级制度中处于低位,人们会产生压力和焦虑,引发破坏免疫系统的皮质醇在体内释放。借用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关于美国南部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书名,一些白人工人阶级被剥夺受尊重感,与国家不断改变的文化格格不入,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因此,桑德尔觉得,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政治党派(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对优绩主义的追求,背叛了传统的工人阶级,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官僚治理方式,从而在竞选中失利。比如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70%以上拥有高等学位的选民。
他认为,正是民主党对市场假设和优绩主义不加批判地拥抱,才为特朗普铺平道路。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拜登是36年来第一个没有常春藤大学学位的民主党候选人,这让他在美国大选中获得了某种优势。不过,即使特朗普大选落败,民主党未来也不一定会成功,除非他们重新定义使命,更加关注合理的不满和怨恨,而进步政治在全球化时代做出了贡献。
面对优绩的暴政,桑德尔希望所有公民思考:怎样才能促进人们的共同利益?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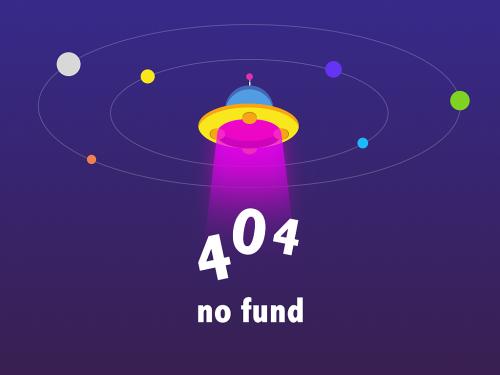
比如,他从大学角色、工作尊严、成功意义三个层面,提了一些建议。
在大学层面,桑德尔觉得,将大学所扮演的角色看成是机会仲裁者,这已经值得商榷了。事实上,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并没有大学学历。因此,创造一个经济体,让大学文凭被看作是获得具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想法相当愚蠢。
当然,他也承认,鼓励人们去念大学是件好事,但得为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提供更多机会。为了让美国人认识到择优录取的运气成分,他甚至提出一种看似激进的方案:所有学生达到给定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参加录取,并可给予额外抽签,以确保多样性。抽签,不仅会让寻求大学录取的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大学录取学生的傲慢。
在工作层面,桑德尔认为,人们应该重塑工作的尊严。工作不仅是在满足温饱,也是在促进公共利益,理应得到认可。
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看法——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标和终结。但是,桑德尔觉得,他们或许忘记古典道德和政治思想传统,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繁荣取决于培养和锻炼我们的能力来实现我们的本性;美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教导说,职业培养公民自治的美德。
所以,我们在经济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作为生产者,我们发展和运用自身能力提供满足同胞所需,赢得社会尊重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所做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用工资来衡量,而取决于努力所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方面的重要性。
为说明这一点,桑德尔打了个比方:想想沃尔特·怀特的两个职业,他是高中化学教师,在美剧《绝命毒师》中变成冰毒大亨。当怀特离开教室,将技能应用于制作冰毒时,挣的钱远远超过他做教师获得的微薄工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作冰毒比做高中老师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谁对共同利益的贡献最大,不能由市场决定,需要民主社会的公民辩论,达成共识,形成道德判断。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很可能改变许多美国人对谁的贡献最重要的感知。我们所依赖的是那些‘基本工人’,但他们是社会中收入最少的成员。”
为强调工作是使公民聚集在一个相互贡献和认可的网络,桑德尔又讲了一个故事。
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几个小时,回想起在田纳西州曼菲斯清洁工人所发起的罢工事件,说:“归根结底,捡垃圾的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他不工作,疾病就会蔓延。所有工作都有其尊严。”
桑德尔称,新冠疫情让这个道理更清楚。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劳动者,如送货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员工、仓库工人、货车司机、护理师助理、育儿员、居家照护业者……这些并不是薪资最好或最光荣的工作者。但现在,我们将他们视为不可或缺的工作者。这是一个开启公共辩论的时刻,讨论如何使他们的薪水,及其所获得的认同,能够与其工作重要性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重塑工作尊严可考虑两个方向的政策:一是对低收入工人的工资补贴,比如政府可根据目标小时工资,为低工资雇员每工作一小时提供一笔补充款;另一方法是降低甚至取消工资税,并通过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交易征税来增加收入。
不过,《华盛顿月刊》一篇评论批评桑德尔遗漏工会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工会的衰落远远超过其他面临类似全球化压力的国家。这种衰落是因为美国法律没有认识到组织劳工是一种公民权利。雇主经常因为员工组织工会解雇他们,但现在对这种手段的惩罚极弱。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国会应将1991年的《民权法》扩大到那些因试图建立工会而被解雇的人。”
最后,在成功意义层面,桑德尔觉得,人们可以扪心自问:“我在道德上应该得到使我蓬勃发展的才能吗?我的成就是否源自于我活在一个奖励才华的社会中,而这个才华是我正好所拥有的?还是只因为我很幸运而已?”
在他看来,坚信成功是因为自身的缘故,让人很难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困境。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会促使我们变得谦卑。或许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或者神的恩典,或者命运的奥秘,所以“我”才能到达某个高度。
他举了个例子:现在人们喜欢篮球,所以,擅长精准投篮就具有极大的市场价值。这也是勒布朗·詹姆斯能赚那么多钱的原因。然而,他只不过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人们热爱篮球的时代。假设他生活在中世纪,具有同样的投篮天赋,但消费者市场完全不同,人们不关心他是否会投篮,而只关心他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战士或牧师,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富有。既然他生活在什么时代、消费者市场会怎样,都不取决于他本人的作为,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说,他应当获得他现在从市场中赚到的那些钱。
“这种谦卑的精神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公民素养。这个契机让我们可以从分裂彼此的成功道德观走回正轨,引领我们超越独裁的优绩体制,走向一个少点怨恨,更加慷慨的公共生活。”桑德尔说。
这几年,英语世界出现了很多批判优绩主义的作品,反思精英统治,这也是桑德尔新书诞生的背景。
它们多从教育角度切入,比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拉妮·吉尼尔(lani guinier)的《优绩制的暴政: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the tyranny of the meritocracy: democratiz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的《优绩制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过渡》(the crisis of the meritocracy: britain’s transition to mass education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how america'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等。
其中,去年出版的《优绩制的陷阱》受到许多关注和讨论。作者马科维茨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的主要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所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优绩制只是一个陷阱,滋养不平等,瓦解中产阶级,吞噬精英阶层。最终,它促使社会分裂,侵蚀民主政治,推动民粹主义兴起。
在另一个维度上,如果从桑德尔的内在思想脉络出发,《优绩的暴政》和他之前作品实则一脉相承。
在第一本书《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他反对康德式和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们虽然没有讨论技术官僚,但秉持的是正当应该优先于善的观念。而他所赞成的政治主张是善应该优先于正当,因此它必然涉及德性、道德品质和道德教育。
在后来的《民主的不满》中,桑德尔梳理美国的政治传统,试图表明美国国父们在建国之初曾非常热衷于培养公民德性。但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政治争论转向了康德和罗尔斯式的观念,德性的成分被排挤了。最近几十年,德性的成分消失,技术官僚和专家获得统治地位。
到了《金钱不能买什么》,他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市场和市场价值观逐渐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们的生活。但这存在问题,某些社会领域不应该由市场思维介入,人们需要认真思考市场的道德局限性,形成更健康的公共生活。
目睹这些年的政治变化,深感公民德性和共同利益讨论的缺失,他才写下《优绩的暴政》。
有意思的是,以批判罗尔斯成名的桑德尔,同意罗尔斯关于运气的观点:由竞争性市场所界定的经济回报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因此不能说,人们在道德上应当获得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所赚到的一切。
但是,他不同意罗尔斯认为分配正义和优绩无关,觉得在分配正义中可以有优绩,只要这种优绩是根据道德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根据市场的共同利益来界定。比如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多半会赞同,教师或医生在道德上应当比华尔街投机者们得到更多报酬。
“如果有人质问我:当人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究竟如何推理共同利益?对此,我的回应是:让我们一个个地来。我会问:如果说给赌徒提供赌场的那些人所具有的价值或道德重要性,比不上那些治病救人的医生或教书育人的教师,你们会同意吗?也许,我们在很多地方无法达成一致,但我们也会找到一些普遍的原则。在我看来,认为我们完全无法就‘什么是共同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达成一致,并且因此而拒绝任何尝试,这是错误的。”桑德尔说。
这也是桑德尔给我们的启示,你对他的观点同意与否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公共讨论和公民生活。唯在公共讨论中,哲学才最有价值。
“哲学并非大而抽象的问题,而是体现在我们不同的信仰和观点中。如果公众有机会这样坐下来讨论,彼此倾听观点背后的根源,而不是简单的投票,或许我们仍然会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但也有可能受到别人观点的启发而改变,这就是令人兴奋而极具挑战的哲学层面。当我们对曾经坚信的事情动摇的时候,说明我们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参考资料来自《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卫报》《哈佛杂志》《华盛顿月刊》《哲学动态》等。)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