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二战结束后,冷战和殖民主义的解体过程自欧洲-地中海开始顺次展开。两大国际体系在欧洲的竞赛具有意识形态的外表。柏林墙成为分隔两种哲学与生活方式的现实象征。然而在广大亚非拉的冷战边缘,超级大国的代理人斗争则演变为赤裸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实力政治。美苏双方在非洲支持各种派系,主要是为了遏制彼此的势力范围。在这样的限制下,两大强权无力也无意苛求地方代理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选择。殖民主义仓皇撤退留下的真空,结合美苏双方没有道德约束的援助,滋长了去殖民化的非洲大陆几十年的混乱、腐败与欠发达。
冷战终结消解了大国竞争对非洲政治扭曲的一个根源。腐败无能的政府不再能凭借自己的“反苏牌”获得美国无条件的支持来渡过难关。经济压力迫使他们向国际基金组织(imf)等西方机构寻求帮助,而这些机构伸出的橄榄枝,往往附带着各种改革的要求。许多掌权几十年的独裁者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在内外交困下下开启了改革。
蔓延在西方的冷战胜利情绪将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捧上普世发展道路的神坛。前苏东地区相对顺利的转型让许多西方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认定,仅凭“民主化”的理念能为政治发展指出清晰可行的操作手册。刚腾出手来的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援助的思维中,逐渐开始强调价值观的作用。它们把推进西方民主制度视作其重大的道德使命。威权政府也乐于通过开放竞争性选举来打造自己在国际上的新形象,以图重塑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冷战思维所相信的民主-稳定-发展的简单线性关系在非洲复杂的现实面前压根无法成立。新兴的非洲民主化往往是脆弱、破碎的。选举和政治竞争没有带来理想中的贤能负责的政府和各方利益的和谐。选票往往和腐败、冲突甚至内战如影随形。独裁者们很快学会了如何用民主的外表来保留控制的实质。这种对民主价值的阳奉阴违进一步激发了反抗与怒火。从90年代初的科特迪瓦,到今年的埃塞俄比亚,贫穷和动荡的阴影一直在非洲大陆上空徘徊。

《战争、枪炮与选票》
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促使政治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把握和校准民主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经济进步之间的复杂联系。可供利用的大量新案例同样激发了民主化研究新的学术兴趣与方向。以1991年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为代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与21世纪的头十年见证了民主研究经典文献的井喷式发展。“民主化”这一议题如今往往被放置在“国家建构”这个更加宏观的框架中去考察。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系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西方发达国家稳定体制中的日常政治,掩盖了其制度中许多并不明显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通常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得到落实的。而他们也不能绝对地免疫于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变迁所带来的冲击。
后“911”时代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入侵为民主化研究更增添了现实的意义——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建立在对“输出民主”和政治转型的概念相当图像化的理解上。2003年后的研究文献着重警惕对民主化简单、线性的想象,不能说不是对这一现实的某种间接、含蓄的回应。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政治的去稳定化与分化大致印证了这些睿智警告。2016年以来发达民主国中出现的民主去巩固现象,更让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忧虑民主政治的未来。
查尔斯·蒂利曾提出这样一种比喻。大致可以对比极端乐观者和极端悲观者两种思维方式:在乐观者看来,民主就像苗圃里的花朵。只要气候合适、土壤不过于贫瘠,园丁需要做的就是撒下种子,仔细地浇灌和施肥,时不时清除杂草。随后他们就可以等待民主的花朵茁壮开放。这一过程是标准化、可控、清楚明白的。一个熟练的民主园丁只要有足够的善意、耐心和资源,就能把“落后”的政治改造为符合西方理想的模式。民主化没有任何内生的阻碍,正如好树上长不出坏果子;需要做的只是把妨害民主有机成长的“坏成分”清除干净,一切就万事大吉。悲观者与之相反。在他们看来,民主化更像是石油和煤形成的那个过程: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和极其罕见的地理条件的组合,生物的残骸才能在很小的概率下变成可供利用的化石能源。人类的科学技术无力完全解明这一过程,遑论大规模复制。科学能做的只有“勘探”出已经存在的“民主油田”,以适当的方式开发采掘而已。
我们自然的人性总是会过犹不及,在偏离现实的对立极端中反复横跳。弥漫在上世纪末的乐观情绪如今让位给命定论的悲观主义。很多西方政坛老手如今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政治进步的前景有着相当昏暗的看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在《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表达过中东政治之无解局面的失望。在经过训练的学术眼光看来,这同样是不符合现实的简单化和情绪化反应。蒂利在总结极端悲观和极端乐观两种图景之后提出了自己所更偏爱的隐喻:民主化就像是湖泊的形成。每一个湖都有着多少相似的特征和稳定的结构。形成湖泊的地质过程千差万别,没有一定之规,但这些必要的过程会反复发生,可以被科学探究正确地识别出来。它们需要恰当地组合在一起才能发展为造湖运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会无疾而终。
在我看来,一个更好理解的意象或许是“炼金术”:通过反复探究实验记录中的原料、配比、过程和最终结果,研究者把握到了一些大致有效的对应模式和因果联系。炼金术士们——我们的民主化理论家——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尝试对这些联系进行解读,偶尔鼓动那些好奇大胆的人进行一些“小尝试”。这些尝试有些产生意外之喜,更多的时候终结于字面意义的“爆炸性的灾难”。在相当于现代原子-分子理论的社科定律出现之前,我们对民主化的探究仍然没有进入“化学”阶段,然而炼金术的智慧的确也已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这意味着人类的意志和理性并非绝对无所作为。哈耶克的教诲是对的: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建构太多是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行动的非意图后果。因此,对制度和社会进行理性建构和重整面临各种危险和未知。马基雅维利也是对的:通过人类的德性,我们可以征服“命运的女神。”——这不是在为我们理智的愚妄和力量的草率随意开出空头支票。恰恰相反,理智的探究是为了清除迷雾,尽可能弄清我们到底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可以做到什么、不可以做到什么。将不确定性和人类力量的限度勾勒出形状,也就是将随机的盲目纳入意志和目的的领域。我们无法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会遭遇意外,但保险公司的精算会把这个事件呈现为某一相对精确的概率。我们无法在各种孤注一掷和从未遭遇的情境中保证万无一失,但合理的思考与可靠的经验总归能排除那些明显荒谬的奇思妙想,暗示出走出森林的可能路径。
政治学家保罗·科利尔就是这么一位有着现实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炼金术士”。他是研究非洲冲突与民主化转型的顶级权威,在英国政府的非洲政策中享有巨大话语权。同时他也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1998-2003),长期接触事关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经验。柯利尔关于非洲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著作《战争、枪炮与选票》英文版出版于2010年,结合了之前20年民主理论的进展和自身研究,以通俗、准确的笔触描述了为何非洲“全球最底层的十亿人”的民主实践经常带来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陷入现实主义者常见的失败主义和犬儒主义情绪,而是在理解现实的前提下,在可行的政策范围内提出一些或许有效的建议——当“不可能”的界线更加清晰,“可能性”的空间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笃定和希望。
柯利尔首先处理的关于民主的浪漫幻想之一就是民主化会平息社会冲突、带来利益和谐的假设。非洲民主化的实证证据对此没有很好地支撑。根据他在书中引用的自己的课题组的研究,在人均gdp低于2700美元左右的国家,竞争性的选举政治(西方式“民主”最典型的要素)往往对国家发展有着负面的影响。越是在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民主”所能产生的正效应越明显。然而不幸的是,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人均gdp都远低于2700美元这个不高的数额(作为对比: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0美元)。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在非洲造成的破坏有可能会超过其潜在的好处。为何事情竟会如此发展?柯利尔在书中有着简单精辟的解答。他认识到“族群政治”和“国家能力”的缺失是竞争性选举失灵的重要原因。这和政治社会学对民主化的历史之定性考察的初步印象相符合——在学术眼光的透视之下,现代大众民主的形象变得复杂和暧昧,远非大众宣传中的非黑即白。
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中细致地梳理了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自三十年战争后逐渐走向现代民主的历程。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走向稳定民主制的道路不止一条。无论是法国这样通过不断地战争与革命一次次重整政治关系的中央集权型国家,还是英国这种通过渐次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的分权型议会国家,最终都多少形成了广泛、平等、受保护的大众政治参与基础上的负责制政府。但形成民主体制的动力离不开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不同社会和政治的行动者之间反复发生的拉锯战,在一些特殊条件的组合之下会开启民主化的进程。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抗争政治本身带来的社会分裂和动荡,是任何治体都要努力避免的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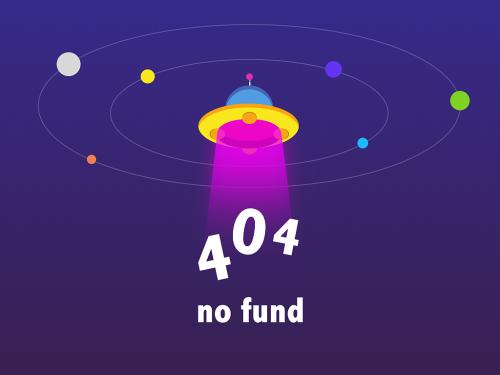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在蒂利看来,民主化涉及几个有时互相冲突的过程的互相配合。简略来说,政府希望对国境内的暴力进行更有效的整合与控制,对社会生产的资源更有效率地汲取,以及加深对臣民之间社会关系的调控。(用蒂利的术语来说,这三种目的分别属于强制、资本与承诺)。统治精英为了以上三个目的所发起的行动,往往引起各种社会不满者的对抗。这些对抗势力也掌握着相应的暴力、资源和社会网络。国家及其臣民之间的对抗有时是个别的、象征性的,还有些时候相当暴烈且广泛。对于民主化来说两者没有绝对优劣之分,关键在于,开启民主化的抗争过程同时改变了国家和臣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国家对暴力之集中和资源攫取的诉求打破了分散的地方势力,废除了特权,制造了行政统一下的平等公民身份,促进了人口流动。通向这一结果的过程如果是在反复斗争的条件下展开,任何一方都没获得决定性胜利,国家就会在得到他想要的能力和资源的同时,给予公民财产和自由方面更坚固的承诺和保护。在公民这一边,与不断扩张的国家的斗争也制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旧有的身份逐渐解体,新的身份逐渐形成。原本封闭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际网络逐渐让位给为共通的利益、理念而服务的动员型政治网络。蒂利将这一过程称为嵌入型身份(embedded identity)的衰落与和脱嵌型身份(detached identity)的兴起。现代民主制下的政党就是这一转型的集中体现。稳定民主中的政党,通常是各个不同利益诉求之集团的组合。它们打破了封闭身份关系所追求的诉求的决定性,更容易和政治对手达成妥协。
最后,如果组织起来的社会各集团能够制造和维持大致的平等,或者将社会上的不平等尽可能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比如坚持无论贵贱一人一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大众民主就算成型了。在这一制度下,抗争性政治被纳入社会和政治规范中,对其既鼓励又限制。社会所能容忍的抗争行动的范畴大大增加了,但它们的暴力程度和烈度则随之大大下降。成功的民主国家将其内部的血腥历史甩在了背后。
总而言之,在合适的条件下,抗争性政治会让国家能力和社会动员彼此促进。政治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去年的新书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中借用了博弈论的概念将之称之为“红皇后竞赛”。
假如我们接受蒂利的看法,将成功的民主化视作特殊的抗争性政治所形成的稀有均衡。那么失败的民主化就必然涉及失去准头的斗争和国家建构的失败。柯利尔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中》将非洲的失败民主化称作“疯狂民主”(democrazy)十分精确地概括了这种现象。其中正是囊括了前文所提到的“国家失灵”和“斗争失准”——这是两个相互独立却互相关联的现象。
国家的无力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无法有效地垄断暴力,其二是无法广泛深入地汲取社会资源。在非洲大多数国家,这两者都让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整个社会过多的资源耗费在防备自己的邻居上,让国家无法暴力垄断的规模效益,也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财政系统贫弱,则削弱了公民和国家通过谈判来规范预算用途的动机。柯利尔在书中提到,非洲国家的政府税收开支只占据gdp很少的份额——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所梦想的小政府天堂。缺少税收首先意味着政府很难正常运转: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组建治安队伍与法庭、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无法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也难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非洲最为贫困弱小的国家通常有低得惊人的入狱率。刚果共和国每十万人中有27人入狱,中非共和国有16人。对比之下,以治安良好著称的挪威每十万人入狱率是60,丹麦是63。这不是因为非洲穷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此之弱,以至于缺乏像样的执法力量,罪犯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审判和惩处。
更为要紧的是,正如蒂利指出国家扩权的过程也是引起公民抗争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样,税收的扩张往往激起公民对政治参与和预算监督的兴趣。这对贪污腐败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柯利尔观察到,比起依赖会受到严重监督的税收预算,非洲国家往往更青睐于从钻石、铜矿、石油之类自然资源中获取收入——而这些矿产恰好是不少非洲国家唯一能在国际市场卖出价格的产品。政治经济学中越是资源丰富就越是陷入贫困的“资源陷阱”,在非洲并不是一句空话。
斗争性政治失去准头造成的后果远为严重。柯利尔正确地指出族群身份的政治化造成的几个问题:1)民主的问责机制被扭曲:人们只通过族群认同来投票,而不是领导人的治理绩效;2)资源的分配缺乏公平和效率:占据政治权力关键地位的族群就能利用国家机器把握社会资源的分配,使其决定性地有利于自身族群,这反过来又让该族群更不情愿分享政治权力;3)不利于建立国家认同:族群的认同割裂全国性动员网络的形成和统一的公民身份形成,阻碍了现代式民族-国家的发展。

《民主的阴暗面》
他所指出的这些弊政并不是非洲民主化过程中最黑暗的一页。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中的描述远为细致和震撼。这本书在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后引起了不少针对其命题的争议和批评,在我看来,这其中不少是出于误读。我们这里无法全面讨论曼提出论点和主张,仅就本文关心的部分来说,我认为曼和蒂利一样捕捉到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核心要素:抗争性的政治动员空间的形成和扩大。这种空间有时来自于国家能力的增强,有时却来自国家能力的减弱。后者正是非洲大陆90年代以来的某种普遍境况——抗争性政治的重新兴起不是针对国家建构增强的回应,而是针对威权统治削弱而产生的变化。
这意味着国家之外的亚政治的网络、身份会得到充分的机会扩张、巩固,并进一步政治化。这在大多数国家,就正好体现为族裔身份的崛起和巩固。这种政治化的族裔认同不是蒂利所说的“脱嵌型身份”,而是他所说的“嵌入型身份。”这本来是保留给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的。
蒂利认为国家之下统一平等的“公民”身份是脱嵌型身份最为极端和模范的样本。因为公民身份不涉及人和人之间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而仅仅代表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法律与政治的抽象联系。但如果从曼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公民-国民身份的塑造不仅仅是个体从地方的、行业的、性别的身份中脱离,获得抽象公民地位的过程,它也同样是将抽象平等的公民重新嵌入“民族共同体”这一整全性身份的过程。这种抽离-嵌入的两面性,一方面容纳了公民内部政治动员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一种想象的同质性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落实。曼将这一过程统一称之为“族群清洗。”现代成熟民主国家的“族群清洗”已是被遗忘的历史。但是在非洲大陆的新兴国家,这一过程却是现在进行时。当族群-民族政治和国家权威削弱所开启的抗争性政治的动员空间互相重合,民主化就进入了危险区。此时抗争性政治就有可能进入危险的升级通道,导致与“民主化”完全相反的对立面、“族群清洗”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种族屠杀。
保罗·柯利尔或许不如迈克尔·曼那样关注“战争、枪炮与选票”的不幸组合带来的最恶劣的结果。但他同样意识到,困扰非洲脆弱的政治循环的关键词是“安全”与“信任”——这两者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产品。迈克尔·曼和查尔斯·蒂利告诉我们,这两者在现代民主的发源地欧洲和美国,都是从头破血流的死路中杀出来的。但如今,非洲国家的民主化不应、也不必走过这些类似的道路。保罗·科利尔大胆又诚恳地指出,比起具体的技术指导和物质援助,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安全”和“信任”是帮助非洲最底层十亿人摆脱恶劣政治最好的礼物。从道义上说,这是曾经的殖民列强所应负的责任;从利益上来说,这些有限的投入经常带来远超成本的回报——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非洲,无疑将会改善整个人类的境况。
二战结束后,冷战和殖民主义的解体过程自欧洲-地中海开始顺次展开。两大国际体系在欧洲的竞赛具有意识形态的外表。柏林墙成为分隔两种哲学与生活方式的现实象征。然而在广大亚非拉的冷战边缘,超级大国的代理人斗争则演变为赤裸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实力政治。美苏双方在非洲支持各种派系,主要是为了遏制彼此的势力范围。在这样的限制下,两大强权无力也无意苛求地方代理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选择。殖民主义仓皇撤退留下的真空,结合美苏双方没有道德约束的援助,滋长了去殖民化的非洲大陆几十年的混乱、腐败与欠发达。
冷战终结消解了大国竞争对非洲政治扭曲的一个根源。腐败无能的政府不再能凭借自己的“反苏牌”获得美国无条件的支持来渡过难关。经济压力迫使他们向国际基金组织(imf)等西方机构寻求帮助,而这些机构伸出的橄榄枝,往往附带着各种改革的要求。许多掌权几十年的独裁者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在内外交困下下开启了改革。
蔓延在西方的冷战胜利情绪将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捧上普世发展道路的神坛。前苏东地区相对顺利的转型让许多西方专家和政策制定者认定,仅凭“民主化”的理念能为政治发展指出清晰可行的操作手册。刚腾出手来的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援助的思维中,逐渐开始强调价值观的作用。它们把推进西方民主制度视作其重大的道德使命。威权政府也乐于通过开放竞争性选举来打造自己在国际上的新形象,以图重塑自身的执政合法性。
冷战思维所相信的民主-稳定-发展的简单线性关系在非洲复杂的现实面前压根无法成立。新兴的非洲民主化往往是脆弱、破碎的。选举和政治竞争没有带来理想中的贤能负责的政府和各方利益的和谐。选票往往和腐败、冲突甚至内战如影随形。独裁者们很快学会了如何用民主的外表来保留控制的实质。这种对民主价值的阳奉阴违进一步激发了反抗与怒火。从90年代初的科特迪瓦,到今年的埃塞俄比亚,贫穷和动荡的阴影一直在非洲大陆上空徘徊。

《战争、枪炮与选票》
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促使政治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把握和校准民主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经济进步之间的复杂联系。可供利用的大量新案例同样激发了民主化研究新的学术兴趣与方向。以1991年塞缪尔·亨廷顿的《第三波》为代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与21世纪的头十年见证了民主研究经典文献的井喷式发展。“民主化”这一议题如今往往被放置在“国家建构”这个更加宏观的框架中去考察。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系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西方发达国家稳定体制中的日常政治,掩盖了其制度中许多并不明显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通常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得到落实的。而他们也不能绝对地免疫于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变迁所带来的冲击。
后“911”时代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入侵为民主化研究更增添了现实的意义——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建立在对“输出民主”和政治转型的概念相当图像化的理解上。2003年后的研究文献着重警惕对民主化简单、线性的想象,不能说不是对这一现实的某种间接、含蓄的回应。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政治的去稳定化与分化大致印证了这些睿智警告。2016年以来发达民主国中出现的民主去巩固现象,更让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忧虑民主政治的未来。
查尔斯·蒂利曾提出这样一种比喻。大致可以对比极端乐观者和极端悲观者两种思维方式:在乐观者看来,民主就像苗圃里的花朵。只要气候合适、土壤不过于贫瘠,园丁需要做的就是撒下种子,仔细地浇灌和施肥,时不时清除杂草。随后他们就可以等待民主的花朵茁壮开放。这一过程是标准化、可控、清楚明白的。一个熟练的民主园丁只要有足够的善意、耐心和资源,就能把“落后”的政治改造为符合西方理想的模式。民主化没有任何内生的阻碍,正如好树上长不出坏果子;需要做的只是把妨害民主有机成长的“坏成分”清除干净,一切就万事大吉。悲观者与之相反。在他们看来,民主化更像是石油和煤形成的那个过程: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和极其罕见的地理条件的组合,生物的残骸才能在很小的概率下变成可供利用的化石能源。人类的科学技术无力完全解明这一过程,遑论大规模复制。科学能做的只有“勘探”出已经存在的“民主油田”,以适当的方式开发采掘而已。
我们自然的人性总是会过犹不及,在偏离现实的对立极端中反复横跳。弥漫在上世纪末的乐观情绪如今让位给命定论的悲观主义。很多西方政坛老手如今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政治进步的前景有着相当昏暗的看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在《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表达过中东政治之无解局面的失望。在经过训练的学术眼光看来,这同样是不符合现实的简单化和情绪化反应。蒂利在总结极端悲观和极端乐观两种图景之后提出了自己所更偏爱的隐喻:民主化就像是湖泊的形成。每一个湖都有着多少相似的特征和稳定的结构。形成湖泊的地质过程千差万别,没有一定之规,但这些必要的过程会反复发生,可以被科学探究正确地识别出来。它们需要恰当地组合在一起才能发展为造湖运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会无疾而终。
在我看来,一个更好理解的意象或许是“炼金术”:通过反复探究实验记录中的原料、配比、过程和最终结果,研究者把握到了一些大致有效的对应模式和因果联系。炼金术士们——我们的民主化理论家——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尝试对这些联系进行解读,偶尔鼓动那些好奇大胆的人进行一些“小尝试”。这些尝试有些产生意外之喜,更多的时候终结于字面意义的“爆炸性的灾难”。在相当于现代原子-分子理论的社科定律出现之前,我们对民主化的探究仍然没有进入“化学”阶段,然而炼金术的智慧的确也已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这意味着人类的意志和理性并非绝对无所作为。哈耶克的教诲是对的: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建构太多是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行动的非意图后果。因此,对制度和社会进行理性建构和重整面临各种危险和未知。马基雅维利也是对的:通过人类的德性,我们可以征服“命运的女神。”——这不是在为我们理智的愚妄和力量的草率随意开出空头支票。恰恰相反,理智的探究是为了清除迷雾,尽可能弄清我们到底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可以做到什么、不可以做到什么。将不确定性和人类力量的限度勾勒出形状,也就是将随机的盲目纳入意志和目的的领域。我们无法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会遭遇意外,但保险公司的精算会把这个事件呈现为某一相对精确的概率。我们无法在各种孤注一掷和从未遭遇的情境中保证万无一失,但合理的思考与可靠的经验总归能排除那些明显荒谬的奇思妙想,暗示出走出森林的可能路径。
政治学家保罗·科利尔就是这么一位有着现实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炼金术士”。他是研究非洲冲突与民主化转型的顶级权威,在英国政府的非洲政策中享有巨大话语权。同时他也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1998-2003),长期接触事关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经验。柯利尔关于非洲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著作《战争、枪炮与选票》英文版出版于2010年,结合了之前20年民主理论的进展和自身研究,以通俗、准确的笔触描述了为何非洲“全球最底层的十亿人”的民主实践经常带来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陷入现实主义者常见的失败主义和犬儒主义情绪,而是在理解现实的前提下,在可行的政策范围内提出一些或许有效的建议——当“不可能”的界线更加清晰,“可能性”的空间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笃定和希望。
柯利尔首先处理的关于民主的浪漫幻想之一就是民主化会平息社会冲突、带来利益和谐的假设。非洲民主化的实证证据对此没有很好地支撑。根据他在书中引用的自己的课题组的研究,在人均gdp低于2700美元左右的国家,竞争性的选举政治(西方式“民主”最典型的要素)往往对国家发展有着负面的影响。越是在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民主”所能产生的正效应越明显。然而不幸的是,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人均gdp都远低于2700美元这个不高的数额(作为对比: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0美元)。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在非洲造成的破坏有可能会超过其潜在的好处。为何事情竟会如此发展?柯利尔在书中有着简单精辟的解答。他认识到“族群政治”和“国家能力”的缺失是竞争性选举失灵的重要原因。这和政治社会学对民主化的历史之定性考察的初步印象相符合——在学术眼光的透视之下,现代大众民主的形象变得复杂和暧昧,远非大众宣传中的非黑即白。
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中细致地梳理了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自三十年战争后逐渐走向现代民主的历程。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走向稳定民主制的道路不止一条。无论是法国这样通过不断地战争与革命一次次重整政治关系的中央集权型国家,还是英国这种通过渐次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的分权型议会国家,最终都多少形成了广泛、平等、受保护的大众政治参与基础上的负责制政府。但形成民主体制的动力离不开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不同社会和政治的行动者之间反复发生的拉锯战,在一些特殊条件的组合之下会开启民主化的进程。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抗争政治本身带来的社会分裂和动荡,是任何治体都要努力避免的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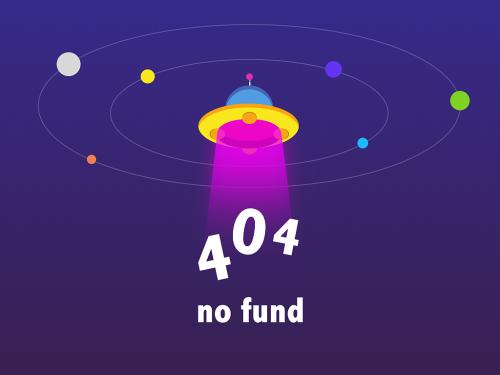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在蒂利看来,民主化涉及几个有时互相冲突的过程的互相配合。简略来说,政府希望对国境内的暴力进行更有效的整合与控制,对社会生产的资源更有效率地汲取,以及加深对臣民之间社会关系的调控。(用蒂利的术语来说,这三种目的分别属于强制、资本与承诺)。统治精英为了以上三个目的所发起的行动,往往引起各种社会不满者的对抗。这些对抗势力也掌握着相应的暴力、资源和社会网络。国家及其臣民之间的对抗有时是个别的、象征性的,还有些时候相当暴烈且广泛。对于民主化来说两者没有绝对优劣之分,关键在于,开启民主化的抗争过程同时改变了国家和臣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国家对暴力之集中和资源攫取的诉求打破了分散的地方势力,废除了特权,制造了行政统一下的平等公民身份,促进了人口流动。通向这一结果的过程如果是在反复斗争的条件下展开,任何一方都没获得决定性胜利,国家就会在得到他想要的能力和资源的同时,给予公民财产和自由方面更坚固的承诺和保护。在公民这一边,与不断扩张的国家的斗争也制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旧有的身份逐渐解体,新的身份逐渐形成。原本封闭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际网络逐渐让位给为共通的利益、理念而服务的动员型政治网络。蒂利将这一过程称为嵌入型身份(embedded identity)的衰落与和脱嵌型身份(detached identity)的兴起。现代民主制下的政党就是这一转型的集中体现。稳定民主中的政党,通常是各个不同利益诉求之集团的组合。它们打破了封闭身份关系所追求的诉求的决定性,更容易和政治对手达成妥协。
最后,如果组织起来的社会各集团能够制造和维持大致的平等,或者将社会上的不平等尽可能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比如坚持无论贵贱一人一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大众民主就算成型了。在这一制度下,抗争性政治被纳入社会和政治规范中,对其既鼓励又限制。社会所能容忍的抗争行动的范畴大大增加了,但它们的暴力程度和烈度则随之大大下降。成功的民主国家将其内部的血腥历史甩在了背后。
总而言之,在合适的条件下,抗争性政治会让国家能力和社会动员彼此促进。政治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去年的新书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中借用了博弈论的概念将之称之为“红皇后竞赛”。
假如我们接受蒂利的看法,将成功的民主化视作特殊的抗争性政治所形成的稀有均衡。那么失败的民主化就必然涉及失去准头的斗争和国家建构的失败。柯利尔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中》将非洲的失败民主化称作“疯狂民主”(democrazy)十分精确地概括了这种现象。其中正是囊括了前文所提到的“国家失灵”和“斗争失准”——这是两个相互独立却互相关联的现象。
国家的无力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无法有效地垄断暴力,其二是无法广泛深入地汲取社会资源。在非洲大多数国家,这两者都让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整个社会过多的资源耗费在防备自己的邻居上,让国家无法暴力垄断的规模效益,也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财政系统贫弱,则削弱了公民和国家通过谈判来规范预算用途的动机。柯利尔在书中提到,非洲国家的政府税收开支只占据gdp很少的份额——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所梦想的小政府天堂。缺少税收首先意味着政府很难正常运转: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组建治安队伍与法庭、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无法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也难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非洲最为贫困弱小的国家通常有低得惊人的入狱率。刚果共和国每十万人中有27人入狱,中非共和国有16人。对比之下,以治安良好著称的挪威每十万人入狱率是60,丹麦是63。这不是因为非洲穷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此之弱,以至于缺乏像样的执法力量,罪犯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审判和惩处。
更为要紧的是,正如蒂利指出国家扩权的过程也是引起公民抗争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样,税收的扩张往往激起公民对政治参与和预算监督的兴趣。这对贪污腐败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柯利尔观察到,比起依赖会受到严重监督的税收预算,非洲国家往往更青睐于从钻石、铜矿、石油之类自然资源中获取收入——而这些矿产恰好是不少非洲国家唯一能在国际市场卖出价格的产品。政治经济学中越是资源丰富就越是陷入贫困的“资源陷阱”,在非洲并不是一句空话。
斗争性政治失去准头造成的后果远为严重。柯利尔正确地指出族群身份的政治化造成的几个问题:1)民主的问责机制被扭曲:人们只通过族群认同来投票,而不是领导人的治理绩效;2)资源的分配缺乏公平和效率:占据政治权力关键地位的族群就能利用国家机器把握社会资源的分配,使其决定性地有利于自身族群,这反过来又让该族群更不情愿分享政治权力;3)不利于建立国家认同:族群的认同割裂全国性动员网络的形成和统一的公民身份形成,阻碍了现代式民族-国家的发展。

《民主的阴暗面》
他所指出的这些弊政并不是非洲民主化过程中最黑暗的一页。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中的描述远为细致和震撼。这本书在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后引起了不少针对其命题的争议和批评,在我看来,这其中不少是出于误读。我们这里无法全面讨论曼提出论点和主张,仅就本文关心的部分来说,我认为曼和蒂利一样捕捉到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核心要素:抗争性的政治动员空间的形成和扩大。这种空间有时来自于国家能力的增强,有时却来自国家能力的减弱。后者正是非洲大陆90年代以来的某种普遍境况——抗争性政治的重新兴起不是针对国家建构增强的回应,而是针对威权统治削弱而产生的变化。
这意味着国家之外的亚政治的网络、身份会得到充分的机会扩张、巩固,并进一步政治化。这在大多数国家,就正好体现为族裔身份的崛起和巩固。这种政治化的族裔认同不是蒂利所说的“脱嵌型身份”,而是他所说的“嵌入型身份。”这本来是保留给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的。
蒂利认为国家之下统一平等的“公民”身份是脱嵌型身份最为极端和模范的样本。因为公民身份不涉及人和人之间具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而仅仅代表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法律与政治的抽象联系。但如果从曼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公民-国民身份的塑造不仅仅是个体从地方的、行业的、性别的身份中脱离,获得抽象公民地位的过程,它也同样是将抽象平等的公民重新嵌入“民族共同体”这一整全性身份的过程。这种抽离-嵌入的两面性,一方面容纳了公民内部政治动员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一种想象的同质性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落实。曼将这一过程统一称之为“族群清洗。”现代成熟民主国家的“族群清洗”已是被遗忘的历史。但是在非洲大陆的新兴国家,这一过程却是现在进行时。当族群-民族政治和国家权威削弱所开启的抗争性政治的动员空间互相重合,民主化就进入了危险区。此时抗争性政治就有可能进入危险的升级通道,导致与“民主化”完全相反的对立面、“族群清洗”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种族屠杀。
保罗·柯利尔或许不如迈克尔·曼那样关注“战争、枪炮与选票”的不幸组合带来的最恶劣的结果。但他同样意识到,困扰非洲脆弱的政治循环的关键词是“安全”与“信任”——这两者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产品。迈克尔·曼和查尔斯·蒂利告诉我们,这两者在现代民主的发源地欧洲和美国,都是从头破血流的死路中杀出来的。但如今,非洲国家的民主化不应、也不必走过这些类似的道路。保罗·科利尔大胆又诚恳地指出,比起具体的技术指导和物质援助,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安全”和“信任”是帮助非洲最底层十亿人摆脱恶劣政治最好的礼物。从道义上说,这是曾经的殖民列强所应负的责任;从利益上来说,这些有限的投入经常带来远超成本的回报——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非洲,无疑将会改善整个人类的境况。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