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盛赞产业政策
我的朋友--弗吉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史蒂夫·罗兹将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1984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的世界观》35周年纪念版,翔实且全面地回顾和解释了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机会成本、边际主义、激励机制、外部性、福利、消费者偏好等等。这些概念的介绍也为该书的最后几节中对经济思想的严厉批判奠定了基础,其中质疑了许多作为其基础的假设,如稳定的偏好、高低品位间的中立性、个人的自私性以及消费者选择的政治自主性。
我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认为它是对该学科的盲目观点的毁灭性批判。尽管新书中包含了许多修订内容,我在阅读修订版时还是觉得它有点过于支持许多传统经济思想,这也是衡量我自己的思想转变程度的一个标准。
现在让我聚焦在一个对于拜登政府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产业政策。这也是政府为全力促进经济增长而对特定经济部门的支持。《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中重复了30年前对产业政策的许多常规的反对意见。政府官僚并不擅长挑选未来的技术;他们没有切身利益在其中,也因此面临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利用其权力来满足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该书指出了许多现实世界中产业政策的失败,如卡特政府对合成燃料的支持或奥巴马政府对索林卓(solyndra)公司的补贴贷款。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成功地运用过产业政策,以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的方式。东亚的快速发展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利用不同形式的产业政策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东亚奇迹》中试图伪称亚洲的成功是由于他们遵循了正统的新古典主义配方,如稳定货币和财政纪律。碰巧为这一年的报告买单的日本人对这些结论不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利用了各种非正统的方式,如定向信贷来加速技术发展。世行被迫修改了研究报告,但修改得非常勉强,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主动承认产业政策可以用来发挥良好的作用。
从关于“发展型国家”的大量文献中得出的下述结论,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产业政策对一个追随早期大国所开辟的道路的后发国家来说效果最好;当它到达技术前沿时,政府确实变得不太能预测市场的未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产业政策作为政策工具在日本和韩国日渐式微的原因。此外,正如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所表明的那样,成功的产业政策取决于某些政治条件,即一个能够充分避免公开的政治压力的高能官僚机构,这就是彼得·埃文(peter evan)所说的 "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
但不仅东亚国家的政府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美国也曾推行了一项产业政策很多年,只是没有被贴上产业政策标签。它被称为国防部,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进行尖端技术投资。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基础技术,包括计算机、雷达、半导体、集成电路以及最有名的互联网,都是从政府资助的军事项目开始的。当国防部开始在像f-35这样的项目上花大钱时,政治化就开始了,制造业被分散到尽可能多的国会区。但事实证明,当技术是新的,而且赌注没有那么高时,政府能够像风险资本家一样行事。与亚洲的快速开发商一样,诀窍在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由技术官僚管理的,并设法避免受试图掌控其预算和议程的政治家的影响。
拜登政府正在两个领域推行产业政策,在我看来这两个领域都十分合理。第一项涉及2月份一项行政命令所要求的对高科技供应链的审查,该命令将着眼于半导体、药品、稀土、大容量电池等的采购。这是由新型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半导体和医疗设备的短缺引起的。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此领域仍然严重依赖中国,仅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就占了全球供应量的50%。像英特尔这样的老牌美国公司很早就将其制造业务外包给国外,直到意识到这造成的战略漏洞,才于今年被迫做出改变。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它打算在未来几年内重新整合台湾产业,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它将主导全球的供应。
从汽车到游戏机的供应链所面临的威胁,是高科技竞争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公司华为是5g电信设备的主导供应商。
它唯一真正的对手是瑞典的埃里克森公司(eriksson),该公司产品虽然更安全,但也更昂贵。虽然中国在塑料玩具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可能难以撼动,但绝对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通信开关设备等高科技产品方面也是如此。当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于1996年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剥离出来时,美国还是该领域的主要供应商。但那些年操控话题的经济学家们只对效率感兴趣。朗讯与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 sa)合并,后者随后被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吸收合并。此外,该公司的所有者还可以涉足其他利润更高的行业,比如手机,而且不管怎样使制造业成为可能的庞大供应链和相关知识已经转移到了亚洲。
因此,在无人在意的情况下,制造能力就这样流失了。当时没有人想到,如果世界地缘政治重新两极化,物理位置会造成很大的不同。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文章所指出的,高科技磁铁和生产它们所需的稀土也是如此。因此,现如今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工业政策来减少在这些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政府考虑产业政策的第二个领域是努力加快向低碳经济的过渡。在我看来,美国目前所处的位置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或60年代的韩国:有一条相当容易预见的技术转型之路。虽然氢气可能是未来的燃料,但目前前景相当遥远。我们已经在迈向一个由替代品和电池驱动的电力万能的未来,而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加速这一进程。拜登政府宣布的基础设施计划包含用于补贴全国范围内的充电站的资金,而目前缺乏充电站是阻碍消费者更快地使用电动汽车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政府决定在任何事情上花费大量资金时,总是存在政治化的风险。我们过去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以及如果一个大型的基础设施倡议真的实现了,我们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种情况,将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以美国的方式建设基础设施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产业政策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在政府发放投资资金的情况下,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即资金的分配不是基于可能的经济回报,而是作为赞助政客的一种形式。这一直是所有国有企业的致命弱点,它们往往优先考虑政治支持者的工作多于考虑利润。
如果拜登政府对其基础设施倡议是认真的,并且实际上能够从国会获得一些资金来支持它,它将不得不仔细考虑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合理的方式分配这些资金,第二个问题是清理如今围绕这些项目的繁文缛节。
毫无疑问,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赤字。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定期公布国家需求和实际支出之间的资金缺口预估;最新数字是5.6万亿美元。这个国家道路、机场和桥梁的糟糕状况对任何从欧洲或亚洲进入美国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产品,至少两党理论上一致认为需要做些什么。不过也可能两党合谋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共和党人不想花费纳税人的钱来解决问题,而民主党人也想让项目夭折。
特朗普政府上任时承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却成为如何不投资基础设施的教科书式案例。特朗普认为这种支出是一种奖励朋友和惩罚敌人的方式。在奥巴马政府末期,纽约州和联邦政府就曾达成协议,共同资助 “门户计划”(gateway program),通过在哈德逊河下修建一条新的隧道来连接纽约和新泽西,从而重振东北走廊。特朗普政府通过改变了成本分担公式使其变得不可行,人们强烈怀疑这样做是为了报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和控制该州政治的民主党人。

插图由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办公室提供
尽管国会拒绝为他的边境墙拨款,特朗普还是动用了国防部的建设资金。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将发现更多基础设施资源政治化配置的例子。
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已经想出了更好的方法来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些方法使它们脱离了政客们的短期计算。例如,澳大利亚有一个由职业官员组成的联邦办公室,他们编制了一份全国范围内主要基础设施提案的清单,然后根据经济影响、与国家优先事项的一致性和可实施性对其进行优先排序。政治家们控制着最终的支出决策,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部的建议。
美国并不是这样做的。基础设施一直是“政治分肥”(pork barrel politics)的典型场合,在有专款专用的时代,通过把一座桥或一个会议中心投入资金混合来购买通过立法所需的选票,就可以完成立法。我记得我定期从弗吉尼亚州北部去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学院的一个辅助护理机构看望我的母亲,然后从99号州际公路(“bud shuster highway”)返回,这条公路连接着州立大学和阿尔托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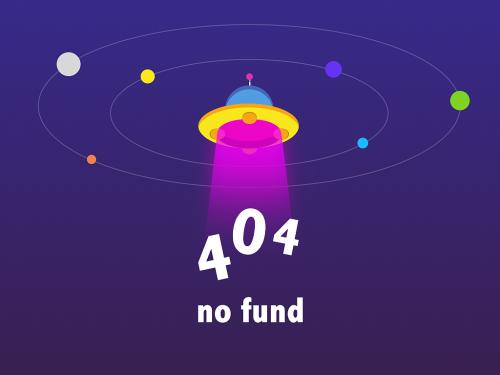
99号州际公路
这是一条美丽的现代高速公路,上面从来没有任何汽车。它也从未连接过任何主要的人口中心,而且实际上违反了国家州际编号系统。它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巴德·舒斯特(bud shuster)是众议院交通委员会的有力主席,负责撰写资助法案,而这条公路穿过他的选区。
拜登总统在4月初宣布的基础设施计划作为其 "美国就业计划 "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钦佩。就像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该计划规模宏大,雄心勃勃,达到了1.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实际上是需要支出的大致数额。他的新任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以及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受命为这一方案游说,并帮助其通过持怀疑态度的国会。
然而,尚不清楚的是,无论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法案,都会反映出一个确定国家优先事项的合理过程。该倡议的宣布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夺,将每个政客最喜欢的项目都塞进法案。拜登不会以特朗普的方式将支出政治化,让项目只流向在选举中支持他的蓝色州。然而,民主党人还有其他方法将基础设施法案政治化,他们利用这些法案来实现其他社会政策目标,如提高少数族裔就业率或鼓励女性所有的企业,或将环境立法伪装成基础设施支出。共和党人批评该提案将基础设施的定义扩大包括对家庭护理人员或工人再培训的支持等内容。
这并不是说像提议的那样的大规模支出法案不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花这么多钱却不把能源转型考虑进去是很疯狂的,我们不需要建造更多的管道和燃煤发电厂。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需要有一个国家计划,来列出相互竞争的目标并制定明确的优先次序,让纳税人看到正在权衡的事项。增加对少数族裔或工会雇用的要求,或进一步的环境检查,将推迟并大幅增加新项目的成本而且直到事后才会显现出来。也许他们值得,但提前知道他们的成本会有所帮助。
这也带来了与官僚主义有关的第二个挑战。目前基础设施项目已经陷入了一个晦涩复杂的过程,需要多达15个联邦机构批准,而且这些批准必须按顺序而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一个机构在过程的最后阶段提出异议,整个过程就需要从头开始,这还只是联邦部分。在许多州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州机构重复前述这些认证的重复程序。根据《加州环境质量法》(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该州的每个公民都有资格匿名起诉任何特定的项目,没有法定时效限制。
美国将永远无法像澳大利亚那样,对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从理论上讲,建立一个基础设施银行可能是件好事,我们可以依靠它来审查项目并推荐优先事项。但美国宪法确定了国会开支的责任,而要想从这个两极分化的机构中获得任何形式的立法总是需要混乱的妥协和回报。事实上,许多国会观察家认为,取消专项拨款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要在未来完成任何事情,有所作为,我们需要回到某种形式的“政治分肥”。
尽管如此,如果拜登政府真的想修复美国的基础设施,并利用这项支出来刺激就业和生产力的增长,它就需要解决审查和实施提案的行政程序。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措施可以用来简化和加快审批,而不用牺牲每个人都认为是可取的环境和社会目标。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实现这些非经济目标的愿望将会给已经十分繁重的、自我损坏的过程再增加一层规则和检查。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
盛赞产业政策
我的朋友--弗吉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史蒂夫·罗兹将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1984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的世界观》35周年纪念版,翔实且全面地回顾和解释了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机会成本、边际主义、激励机制、外部性、福利、消费者偏好等等。这些概念的介绍也为该书的最后几节中对经济思想的严厉批判奠定了基础,其中质疑了许多作为其基础的假设,如稳定的偏好、高低品位间的中立性、个人的自私性以及消费者选择的政治自主性。
我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认为它是对该学科的盲目观点的毁灭性批判。尽管新书中包含了许多修订内容,我在阅读修订版时还是觉得它有点过于支持许多传统经济思想,这也是衡量我自己的思想转变程度的一个标准。
现在让我聚焦在一个对于拜登政府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产业政策。这也是政府为全力促进经济增长而对特定经济部门的支持。《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中重复了30年前对产业政策的许多常规的反对意见。政府官僚并不擅长挑选未来的技术;他们没有切身利益在其中,也因此面临扭曲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利用其权力来满足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该书指出了许多现实世界中产业政策的失败,如卡特政府对合成燃料的支持或奥巴马政府对索林卓(solyndra)公司的补贴贷款。
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成功地运用过产业政策,以经济学家们并不认同的方式。东亚的快速发展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利用不同形式的产业政策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东亚奇迹》中试图伪称亚洲的成功是由于他们遵循了正统的新古典主义配方,如稳定货币和财政纪律。碰巧为这一年的报告买单的日本人对这些结论不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利用了各种非正统的方式,如定向信贷来加速技术发展。世行被迫修改了研究报告,但修改得非常勉强,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主动承认产业政策可以用来发挥良好的作用。
从关于“发展型国家”的大量文献中得出的下述结论,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产业政策对一个追随早期大国所开辟的道路的后发国家来说效果最好;当它到达技术前沿时,政府确实变得不太能预测市场的未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产业政策作为政策工具在日本和韩国日渐式微的原因。此外,正如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所表明的那样,成功的产业政策取决于某些政治条件,即一个能够充分避免公开的政治压力的高能官僚机构,这就是彼得·埃文(peter evan)所说的 "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
但不仅东亚国家的政府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美国也曾推行了一项产业政策很多年,只是没有被贴上产业政策标签。它被称为国防部,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进行尖端技术投资。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基础技术,包括计算机、雷达、半导体、集成电路以及最有名的互联网,都是从政府资助的军事项目开始的。当国防部开始在像f-35这样的项目上花大钱时,政治化就开始了,制造业被分散到尽可能多的国会区。但事实证明,当技术是新的,而且赌注没有那么高时,政府能够像风险资本家一样行事。与亚洲的快速开发商一样,诀窍在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由技术官僚管理的,并设法避免受试图掌控其预算和议程的政治家的影响。
拜登政府正在两个领域推行产业政策,在我看来这两个领域都十分合理。第一项涉及2月份一项行政命令所要求的对高科技供应链的审查,该命令将着眼于半导体、药品、稀土、大容量电池等的采购。这是由新型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半导体和医疗设备的短缺引起的。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此领域仍然严重依赖中国,仅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就占了全球供应量的50%。像英特尔这样的老牌美国公司很早就将其制造业务外包给国外,直到意识到这造成的战略漏洞,才于今年被迫做出改变。中国大陆已经宣布,它打算在未来几年内重新整合台湾产业,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它将主导全球的供应。
从汽车到游戏机的供应链所面临的威胁,是高科技竞争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公司华为是5g电信设备的主导供应商。
它唯一真正的对手是瑞典的埃里克森公司(eriksson),该公司产品虽然更安全,但也更昂贵。虽然中国在塑料玩具生产方面的主导地位可能难以撼动,但绝对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通信开关设备等高科技产品方面也是如此。当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于1996年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剥离出来时,美国还是该领域的主要供应商。但那些年操控话题的经济学家们只对效率感兴趣。朗讯与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 sa)合并,后者随后被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吸收合并。此外,该公司的所有者还可以涉足其他利润更高的行业,比如手机,而且不管怎样使制造业成为可能的庞大供应链和相关知识已经转移到了亚洲。
因此,在无人在意的情况下,制造能力就这样流失了。当时没有人想到,如果世界地缘政治重新两极化,物理位置会造成很大的不同。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文章所指出的,高科技磁铁和生产它们所需的稀土也是如此。因此,现如今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工业政策来减少在这些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政府考虑产业政策的第二个领域是努力加快向低碳经济的过渡。在我看来,美国目前所处的位置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或60年代的韩国:有一条相当容易预见的技术转型之路。虽然氢气可能是未来的燃料,但目前前景相当遥远。我们已经在迈向一个由替代品和电池驱动的电力万能的未来,而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加速这一进程。拜登政府宣布的基础设施计划包含用于补贴全国范围内的充电站的资金,而目前缺乏充电站是阻碍消费者更快地使用电动汽车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政府决定在任何事情上花费大量资金时,总是存在政治化的风险。我们过去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以及如果一个大型的基础设施倡议真的实现了,我们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种情况,将是我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以美国的方式建设基础设施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产业政策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在政府发放投资资金的情况下,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即资金的分配不是基于可能的经济回报,而是作为赞助政客的一种形式。这一直是所有国有企业的致命弱点,它们往往优先考虑政治支持者的工作多于考虑利润。
如果拜登政府对其基础设施倡议是认真的,并且实际上能够从国会获得一些资金来支持它,它将不得不仔细考虑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合理的方式分配这些资金,第二个问题是清理如今围绕这些项目的繁文缛节。
毫无疑问,美国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赤字。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定期公布国家需求和实际支出之间的资金缺口预估;最新数字是5.6万亿美元。这个国家道路、机场和桥梁的糟糕状况对任何从欧洲或亚洲进入美国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产品,至少两党理论上一致认为需要做些什么。不过也可能两党合谋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共和党人不想花费纳税人的钱来解决问题,而民主党人也想让项目夭折。
特朗普政府上任时承诺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却成为如何不投资基础设施的教科书式案例。特朗普认为这种支出是一种奖励朋友和惩罚敌人的方式。在奥巴马政府末期,纽约州和联邦政府就曾达成协议,共同资助 “门户计划”(gateway program),通过在哈德逊河下修建一条新的隧道来连接纽约和新泽西,从而重振东北走廊。特朗普政府通过改变了成本分担公式使其变得不可行,人们强烈怀疑这样做是为了报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和控制该州政治的民主党人。

插图由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办公室提供
尽管国会拒绝为他的边境墙拨款,特朗普还是动用了国防部的建设资金。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将发现更多基础设施资源政治化配置的例子。
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已经想出了更好的方法来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些方法使它们脱离了政客们的短期计算。例如,澳大利亚有一个由职业官员组成的联邦办公室,他们编制了一份全国范围内主要基础设施提案的清单,然后根据经济影响、与国家优先事项的一致性和可实施性对其进行优先排序。政治家们控制着最终的支出决策,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部的建议。
美国并不是这样做的。基础设施一直是“政治分肥”(pork barrel politics)的典型场合,在有专款专用的时代,通过把一座桥或一个会议中心投入资金混合来购买通过立法所需的选票,就可以完成立法。我记得我定期从弗吉尼亚州北部去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学院的一个辅助护理机构看望我的母亲,然后从99号州际公路(“bud shuster highway”)返回,这条公路连接着州立大学和阿尔托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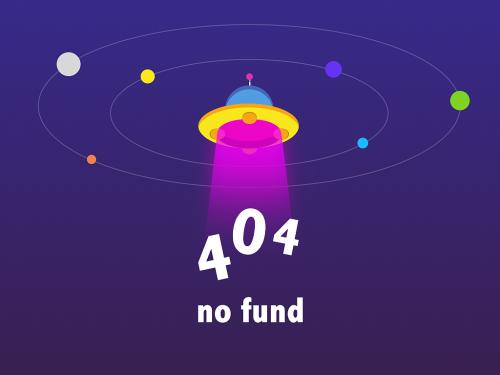
99号州际公路
这是一条美丽的现代高速公路,上面从来没有任何汽车。它也从未连接过任何主要的人口中心,而且实际上违反了国家州际编号系统。它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巴德·舒斯特(bud shuster)是众议院交通委员会的有力主席,负责撰写资助法案,而这条公路穿过他的选区。
拜登总统在4月初宣布的基础设施计划作为其 "美国就业计划 "的一部分,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钦佩。就像他的经济刺激计划一样,该计划规模宏大,雄心勃勃,达到了1.9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实际上是需要支出的大致数额。他的新任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以及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受命为这一方案游说,并帮助其通过持怀疑态度的国会。
然而,尚不清楚的是,无论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法案,都会反映出一个确定国家优先事项的合理过程。该倡议的宣布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夺,将每个政客最喜欢的项目都塞进法案。拜登不会以特朗普的方式将支出政治化,让项目只流向在选举中支持他的蓝色州。然而,民主党人还有其他方法将基础设施法案政治化,他们利用这些法案来实现其他社会政策目标,如提高少数族裔就业率或鼓励女性所有的企业,或将环境立法伪装成基础设施支出。共和党人批评该提案将基础设施的定义扩大包括对家庭护理人员或工人再培训的支持等内容。
这并不是说像提议的那样的大规模支出法案不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花这么多钱却不把能源转型考虑进去是很疯狂的,我们不需要建造更多的管道和燃煤发电厂。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需要有一个国家计划,来列出相互竞争的目标并制定明确的优先次序,让纳税人看到正在权衡的事项。增加对少数族裔或工会雇用的要求,或进一步的环境检查,将推迟并大幅增加新项目的成本而且直到事后才会显现出来。也许他们值得,但提前知道他们的成本会有所帮助。
这也带来了与官僚主义有关的第二个挑战。目前基础设施项目已经陷入了一个晦涩复杂的过程,需要多达15个联邦机构批准,而且这些批准必须按顺序而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一个机构在过程的最后阶段提出异议,整个过程就需要从头开始,这还只是联邦部分。在许多州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州机构重复前述这些认证的重复程序。根据《加州环境质量法》(californi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该州的每个公民都有资格匿名起诉任何特定的项目,没有法定时效限制。
美国将永远无法像澳大利亚那样,对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从理论上讲,建立一个基础设施银行可能是件好事,我们可以依靠它来审查项目并推荐优先事项。但美国宪法确定了国会开支的责任,而要想从这个两极分化的机构中获得任何形式的立法总是需要混乱的妥协和回报。事实上,许多国会观察家认为,取消专项拨款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要在未来完成任何事情,有所作为,我们需要回到某种形式的“政治分肥”。
尽管如此,如果拜登政府真的想修复美国的基础设施,并利用这项支出来刺激就业和生产力的增长,它就需要解决审查和实施提案的行政程序。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措施可以用来简化和加快审批,而不用牺牲每个人都认为是可取的环境和社会目标。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实现这些非经济目标的愿望将会给已经十分繁重的、自我损坏的过程再增加一层规则和检查。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