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苏联的成立与解体均与东斯拉夫(east slavs)三大民族(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共同历史记忆”的传承及“利益纽带关系”的改变密切相关,其中包括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同盟国所签署的《布列斯特条约》(treaty of brest),1922年四国签署的《苏联成立条约》(treaty o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great famine),1945年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victory day),1954年《佩列亚斯拉夫条约》(pereyaslav council)签署三百周年之移交克里米亚,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chernobyl disaster),1991年俄白乌三国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belovezh accords),以及分别爆发于2014年和2022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与普京发动的俄乌战争。
二十世纪初以来,发生在东欧地区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东斯拉夫各民族国家间的整合与重构进程,时而相互融合,时而决裂对抗,直至普京于2月24日宣布启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为止。自此,“俄乌百年友谊”不仅烟消云散,而且还再次敲响了震惊全球的警钟,告知世界“俄国威胁论”已不再是潜在或可能的威胁,相反则是既定事实。
不同以往的是,此次伴随“俄国威胁论”一同浮出水面的是“俄裔威胁论”,即生活在原苏联空间的所有俄罗斯族后裔作为俄国境外“潜在政治工具”所难以预测的实际威胁。“双俄威胁论”的影响力伴随俄乌军事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而日益兴起,并首当其冲地波及俄国分别以“大俄罗斯主义”(great russianism)和“欧亚主义”(eurasianism)为核心的国体根基与区域一体化之现有格局。而在此演变过程中,“俄属乌克兰记忆”的重构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改变原有之地缘平衡。
新旧“大俄罗斯主义”的兴起与覆灭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的成功与一九二二年苏维埃联邦的成立虽表面上将沙俄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基本根除,但事实上则通过新联盟的方式保留了其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与相互之间连贯的“族际关系”。列宁(vladimir lenin)在继承由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为有效分化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而“一手创造”之白俄罗斯(belarus)的同时,将构建沙俄欧陆地缘政治之基础的大俄罗斯(great russian)与小俄罗斯(little russian)彻底一分为二。一方面使以基辅为中心的小俄罗斯“演变”为带有“边缘”意涵的乌克兰,另一方面则让原属圣彼德堡(saint peterburg)的大俄罗斯迁都至内陆莫斯科,并保留其“正统”之名。
不难看出,苏联最高领导层所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在未触碰“大俄罗斯主义”之地缘精髓的前提下从民族文化层面上将东斯拉夫三族进行“分割”。因此,莫斯科中央凭借其“中心—边缘”政策,通过制定统一的政治体制与互补的经济结构维系着俄白乌三国之间巩固且稳定的“核心三角关系”,直至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启先经济后政治的“体制性改革”(perestroika)。
受“戈式改革”洗礼的俄罗斯联邦虽然基本继承原苏联政治与经济遗产的基础,然而并未彻底恢复沙俄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相反则“脚踏两条船”,即以原苏联所构建地缘政治格局为根基部分恢复沙俄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而维系东斯拉夫三族间新构建的“国际关系”,而非原先的“族际关系”。而现阶段普京在发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所发表的讲话则基本否定了苏联所遗留的地缘政治“遗产”。即便如此,普京也未彻底光复沙俄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只是调整了苏联地缘“遗产”与沙俄精神“遗产”之间的比例。
新旧“乌克兰记忆”的构建与绞杀
自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左右东欧原苏联地缘空间发展走向的“乌克兰记忆”在苏联解体之前可谓南辕北辙,城镇上层精英与农村基层民众所分别享有的“共同记忆”可谓勉强挂鈎,双方享有不同等级的待遇,包括所属语言都被细分为城镇语言(俄语)和农村语言(乌克兰语)。总体而言,十月革命之前的“俄乌百年友好关系”是建立在看得见但却模糊不清的“遥远历史”基础之上,而相比之下革命后的“俄乌关系”则是建立在感受得到但却难以说清的“复杂现实”基础之上。
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与当今乌克兰危机的愈演愈烈将原本就要快瓦解的“俄乌共同记忆”彻底掩埋在战火的废墟之中,迫使其乌克兰基辅“抵抗政府”随即着手建构一个完全独立于莫斯科且彻底能够连接上层精英与基层民众的新多元“乌克兰记忆”。相较而言,“新记忆”中的俄罗斯不再是过去有福共享且有难同当的“孪生兄弟”,相反则是无时无刻都倾向于剥夺并侵略乌克兰独立与领土的“致命威胁”。
“乌克兰记忆”之多重地缘战略影响
建立在“回归欧洲”基础之上的“新乌克兰记忆”经过战火的洗礼已将其影响直接反射至区域相连的地缘板块,其效果因国而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新乌克兰记忆”是唤醒民族觉醒和反抗入侵,凝聚人民力量并争取自由,以及构建自上而下的新民族国家之“顶梁柱”。而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乌克兰的新“民族记忆”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威胁”,而且还是“冲击”现有国体之根基的“暗流”,可谓“防不胜防”,因此必须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相比之下,对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而言,“新乌克兰记忆”是防范于未然的“实践经验”。伴随“终止战争”、“荣耀归乌克兰”、“天佑永恆之国乌克兰”、“俄罗斯舰船见鬼去”、“退出集体安全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和“退出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等口号在独联体各国中日益深入人心,以及源自欧美各国所施加的“间接”制裁压力日益凸显,与俄国关系密切的各国上层统治精英不得不重新看待现阶段这“极为棘手的短期地缘战略布局之相关调整问题”。
譬如,身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及盟友的哈萨克斯坦为避免欧美制裁“殃及”自身而允许身居哈萨克的上千名海内外各国“反战爱国人士”于3月6日聚集在共和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almaty)一座专门集中摆放原苏联名人纪念碑的小型广场,为声援“自由乌克兰”举行合法集会。阿克奥尔达(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如此决定被外界普遍视之为史无前例的破天荒之举,是澄清自身与俄罗斯之间“距离”的首次公开信号。
“战后”东欧新地缘政经格局
此轮俄国“定点式清除”军事行动的核心目的并非是将乌克兰彻底“吞併”或以第聂伯河(dnieper)为中心将其“一分为二”。相反,克里姆林宫此次“特别军事行动”的实际目标是在实现与基辅之间“国防脱钩”的基础上,逐渐通过强有力的军事压力,迫使亲欧乌克兰现有之政权签署俄版《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arsailles),将俄军以“非军事化”为名占领的原军工地区转变为类似于德国魏玛(weimar republic)时期的“莱茵兰非军事区或占领领区”(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进而有效遏阻北约进一步的“东扩”。
可是需明确指出,俄版“莱茵兰占领模式”假设一旦取得成功,那俄国将在短期内处于被动的“喘息恢复状态”,虽会有限失去区域地缘经济相关议题的话语权,但会凭借“基本未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养精蓄锐,通过全方位经营以里海(caspian sea)为中心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持续提高自身国际政治与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即军事外交、能源外交、粮食外交、运输外交等。
新地缘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西方各国针对俄国的连续制裁基本上已“冻结了”由俄国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中亚(central asia)段的扩充计划,相反则开启了欧盟在东欧段的新一轮扩充进程。身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格鲁吉亚(georgia)与摩尔达维亚(moldova)虽在此次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虽均“立即”申请加入欧盟,但一如既往,阻碍上述三国加入欧盟的“绊脚石”依旧是一方面难以夺回的“占领叛区”,另一方面则是难以舍去的“主权领土”。
如何根除所有在欧盟候选国中“安插”的敌对“遥控政权”,以及防范其再度重演则是接下来欧盟与北约在持续东扩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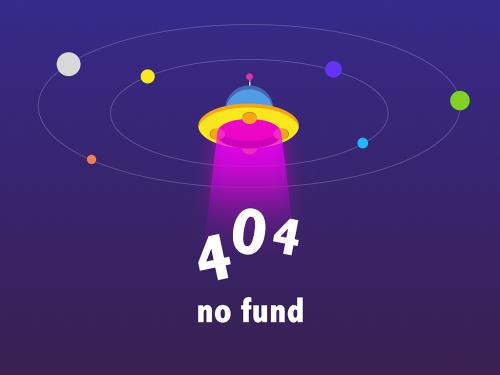
苏联的成立与解体均与东斯拉夫(east slavs)三大民族(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共同历史记忆”的传承及“利益纽带关系”的改变密切相关,其中包括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同盟国所签署的《布列斯特条约》(treaty of brest),1922年四国签署的《苏联成立条约》(treaty on the creation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great famine),1945年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victory day),1954年《佩列亚斯拉夫条约》(pereyaslav council)签署三百周年之移交克里米亚,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chernobyl disaster),1991年俄白乌三国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belovezh accords),以及分别爆发于2014年和2022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与普京发动的俄乌战争。
二十世纪初以来,发生在东欧地区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东斯拉夫各民族国家间的整合与重构进程,时而相互融合,时而决裂对抗,直至普京于2月24日宣布启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为止。自此,“俄乌百年友谊”不仅烟消云散,而且还再次敲响了震惊全球的警钟,告知世界“俄国威胁论”已不再是潜在或可能的威胁,相反则是既定事实。
不同以往的是,此次伴随“俄国威胁论”一同浮出水面的是“俄裔威胁论”,即生活在原苏联空间的所有俄罗斯族后裔作为俄国境外“潜在政治工具”所难以预测的实际威胁。“双俄威胁论”的影响力伴随俄乌军事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而日益兴起,并首当其冲地波及俄国分别以“大俄罗斯主义”(great russianism)和“欧亚主义”(eurasianism)为核心的国体根基与区域一体化之现有格局。而在此演变过程中,“俄属乌克兰记忆”的重构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改变原有之地缘平衡。
新旧“大俄罗斯主义”的兴起与覆灭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的成功与一九二二年苏维埃联邦的成立虽表面上将沙俄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基本根除,但事实上则通过新联盟的方式保留了其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与相互之间连贯的“族际关系”。列宁(vladimir lenin)在继承由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为有效分化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而“一手创造”之白俄罗斯(belarus)的同时,将构建沙俄欧陆地缘政治之基础的大俄罗斯(great russian)与小俄罗斯(little russian)彻底一分为二。一方面使以基辅为中心的小俄罗斯“演变”为带有“边缘”意涵的乌克兰,另一方面则让原属圣彼德堡(saint peterburg)的大俄罗斯迁都至内陆莫斯科,并保留其“正统”之名。
不难看出,苏联最高领导层所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在未触碰“大俄罗斯主义”之地缘精髓的前提下从民族文化层面上将东斯拉夫三族进行“分割”。因此,莫斯科中央凭借其“中心—边缘”政策,通过制定统一的政治体制与互补的经济结构维系着俄白乌三国之间巩固且稳定的“核心三角关系”,直至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启先经济后政治的“体制性改革”(perestroika)。
受“戈式改革”洗礼的俄罗斯联邦虽然基本继承原苏联政治与经济遗产的基础,然而并未彻底恢复沙俄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相反则“脚踏两条船”,即以原苏联所构建地缘政治格局为根基部分恢复沙俄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而维系东斯拉夫三族间新构建的“国际关系”,而非原先的“族际关系”。而现阶段普京在发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所发表的讲话则基本否定了苏联所遗留的地缘政治“遗产”。即便如此,普京也未彻底光复沙俄时期的“大俄罗斯主义”,只是调整了苏联地缘“遗产”与沙俄精神“遗产”之间的比例。
新旧“乌克兰记忆”的构建与绞杀
自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左右东欧原苏联地缘空间发展走向的“乌克兰记忆”在苏联解体之前可谓南辕北辙,城镇上层精英与农村基层民众所分别享有的“共同记忆”可谓勉强挂鈎,双方享有不同等级的待遇,包括所属语言都被细分为城镇语言(俄语)和农村语言(乌克兰语)。总体而言,十月革命之前的“俄乌百年友好关系”是建立在看得见但却模糊不清的“遥远历史”基础之上,而相比之下革命后的“俄乌关系”则是建立在感受得到但却难以说清的“复杂现实”基础之上。
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与当今乌克兰危机的愈演愈烈将原本就要快瓦解的“俄乌共同记忆”彻底掩埋在战火的废墟之中,迫使其乌克兰基辅“抵抗政府”随即着手建构一个完全独立于莫斯科且彻底能够连接上层精英与基层民众的新多元“乌克兰记忆”。相较而言,“新记忆”中的俄罗斯不再是过去有福共享且有难同当的“孪生兄弟”,相反则是无时无刻都倾向于剥夺并侵略乌克兰独立与领土的“致命威胁”。
“乌克兰记忆”之多重地缘战略影响
建立在“回归欧洲”基础之上的“新乌克兰记忆”经过战火的洗礼已将其影响直接反射至区域相连的地缘板块,其效果因国而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新乌克兰记忆”是唤醒民族觉醒和反抗入侵,凝聚人民力量并争取自由,以及构建自上而下的新民族国家之“顶梁柱”。而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乌克兰的新“民族记忆”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威胁”,而且还是“冲击”现有国体之根基的“暗流”,可谓“防不胜防”,因此必须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相比之下,对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而言,“新乌克兰记忆”是防范于未然的“实践经验”。伴随“终止战争”、“荣耀归乌克兰”、“天佑永恆之国乌克兰”、“俄罗斯舰船见鬼去”、“退出集体安全组织”(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和“退出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等口号在独联体各国中日益深入人心,以及源自欧美各国所施加的“间接”制裁压力日益凸显,与俄国关系密切的各国上层统治精英不得不重新看待现阶段这“极为棘手的短期地缘战略布局之相关调整问题”。
譬如,身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及盟友的哈萨克斯坦为避免欧美制裁“殃及”自身而允许身居哈萨克的上千名海内外各国“反战爱国人士”于3月6日聚集在共和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almaty)一座专门集中摆放原苏联名人纪念碑的小型广场,为声援“自由乌克兰”举行合法集会。阿克奥尔达(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如此决定被外界普遍视之为史无前例的破天荒之举,是澄清自身与俄罗斯之间“距离”的首次公开信号。
“战后”东欧新地缘政经格局
此轮俄国“定点式清除”军事行动的核心目的并非是将乌克兰彻底“吞併”或以第聂伯河(dnieper)为中心将其“一分为二”。相反,克里姆林宫此次“特别军事行动”的实际目标是在实现与基辅之间“国防脱钩”的基础上,逐渐通过强有力的军事压力,迫使亲欧乌克兰现有之政权签署俄版《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arsailles),将俄军以“非军事化”为名占领的原军工地区转变为类似于德国魏玛(weimar republic)时期的“莱茵兰非军事区或占领领区”(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进而有效遏阻北约进一步的“东扩”。
可是需明确指出,俄版“莱茵兰占领模式”假设一旦取得成功,那俄国将在短期内处于被动的“喘息恢复状态”,虽会有限失去区域地缘经济相关议题的话语权,但会凭借“基本未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将进一步养精蓄锐,通过全方位经营以里海(caspian sea)为中心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持续提高自身国际政治与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即军事外交、能源外交、粮食外交、运输外交等。
新地缘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西方各国针对俄国的连续制裁基本上已“冻结了”由俄国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中亚(central asia)段的扩充计划,相反则开启了欧盟在东欧段的新一轮扩充进程。身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格鲁吉亚(georgia)与摩尔达维亚(moldova)虽在此次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虽均“立即”申请加入欧盟,但一如既往,阻碍上述三国加入欧盟的“绊脚石”依旧是一方面难以夺回的“占领叛区”,另一方面则是难以舍去的“主权领土”。
如何根除所有在欧盟候选国中“安插”的敌对“遥控政权”,以及防范其再度重演则是接下来欧盟与北约在持续东扩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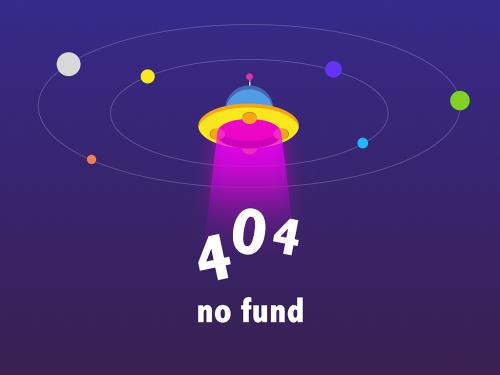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