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世界就是这样吊诡: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已经征服地球万物,正在不断征服大自然,并且一步步征服宇宙,可是,至今却还是拿最低级的生命体病毒没办法。办法是有,譬如打预防针,可不是很灵——打完还是可能被病毒侵害甚至致死;而且,预防针剂的创制很困难,生产过程很复杂,注射过程比较麻烦,因而推进得相当慢。
上文说病毒是“生命体”其实是抬举它了,准确地说,它是“半生命体”。因为,病毒是最原始的生命,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过渡形态。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只是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核酸(dna或rna),没有细胞质和细胞核,不能独立完成生命体的本质特征自复制;只有附着到寄生活细胞的细胞壁上,外壳上的蛋白质毒刺刺破寄生细胞的细胞壁,病毒将自己携带的dna或rna注入寄生细胞,借助寄生细胞的自复制机制,病毒才借尸还魂,开始自己的自复制,表现出生命体的本质特征。一旦离开寄生细胞,病毒单独存在的时候,它只是无生命的结晶体。病毒之所以难对付,可能正是因为它的这种无生命体和生命体的两面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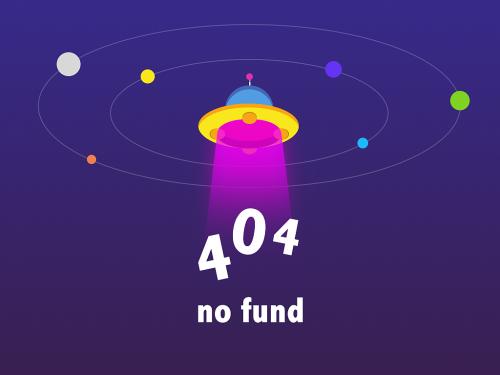
美国辉瑞药厂公布,新研发新冠病毒口服药物的二、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发现成年患者在出现病征后3至5日内服药,重症住院或死亡机会率可以降低89%。美国药管局前局长兼现任辉瑞董事戈特利布也信心预言,美国冠病疫情有望在熬过德尔塔感染潮后,于明年1月初结束。
你看,短短一年半,新冠病毒已经传遍全球20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两亿,患病致死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可是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疫情……在许多国家仍然纷至沓来。需要说明的是,传染疱疹和乙肝之类传染病的是双链dna病毒,一条链发生变异,另一条链对变异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真正发生变异的几率很低;而传染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是单链rna病毒,自身没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发生变异的几率很高。这就是新冠病毒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异的原因。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使用希腊字母命名新冠病毒变异株,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拉姆达……,一个比一个传染力更强,传染更快,传染更广,致死率更高。世卫组织近日又宣布,如果24个希腊字母不够用,要考虑用星座名称命名新冠毒株变体——须知宇宙中星座几乎是无限多呀!因此,人类似乎看不到这场瘟疫终结的希望在何处,终结的时间是何时。看来,人类同病毒决战的时刻真的到来了!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发新的检测手段、新的疫苗和新的药物。人类医学创新能力正在同新冠病毒变异能力赛跑,输赢胜败难说,其结果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刚刚又读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警告说:“未来还可能出现人类根本对付不了的病毒!”此言绝非虚妄,也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真实的威胁。
这不由得令人回望过去几千年人类同上一个死敌细菌的抗争。在地球生命体的阶梯上,细菌比病毒高一个层级,是具有完整细胞结构并能独立复制的单细胞生命体。正因为能独立复制,致病细菌的传染力特别强。鼠疫、霍乱、痢疾、伤寒、脑膜炎、麻风病、白喉、炭疽、肺结核……都是细菌造成的恶性传染病,不知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就拿排第一的鼠疫来说吧。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亚大陆发生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夺走了大约一亿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其中。第二次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的这两句诗,用来描写黑死病肆虐的欧亚大陆是很恰当的。
那么,人类是怎样制伏细菌从而减少直至根绝这些传染病的呢?回答是:靠偶然性。
1928年,英国伦敦的一位医生弗莱明一直在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伤口化脓,多半是葡萄球菌感染。他在一只只培养皿里培养出葡萄球菌,然后试验用各种药剂去杀灭它们。他做这项工作已经好几年,仍然一无所获——这种葡萄球菌实在是个难对付的家伙!9月的一天早晨,弗莱明发现其中一只培养皿里竟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这是因为他开着窗户,肉眼看不见的某种天然霉菌的孢子飞进来,落下去并繁殖起来了。显然,这只培养皿里的培养物被霉菌污染了。弗莱明正要把发了霉的培养物倒掉,突然心生一念:何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啊!”弗莱明大叫一声,马上激动起来:霉斑周围是清澈的,葡萄球菌被杀死了!这不正是梦寐以求的葡萄球菌的克星吗!
他立即动手大量培养这种青绿色的霉菌,将含有霉菌分泌物的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上去。结果,葡萄球菌全部被杀灭。弗莱明把这种培养液叫做青霉素。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季刊上。可是,这篇论文竟未能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弗莱明本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继续研究下去。直到1938年,英国医生佛罗理和钱恩在研究溶菌酶的时候,从检索的文献中发现了弗莱明的那篇文章,并立即着手继续弗莱明当年的研究。这样,青霉素才第二次被发现。佛罗理和钱恩将弗莱明发现的液状霉素加工,经过过滤、浓缩、提纯、干燥,终于得到了一种黄色粉末。1941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青霉素治病的临床试验,结果大获成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大批伤员急需高效抗菌药,在美国的帮助下,青霉素终于能大批量生产,成为一种价格便宜的抗菌特效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1945年,青霉素先后两次被发现的有功之臣——弗莱明、佛罗理、钱恩,一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此后,多种抗生素接连创制出来,人类终于战胜细菌。
有鉴于这个故事,我们似乎只能将战胜病毒的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面: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瞎猫碰死耗子,某一天,又有一个人,碰巧发现一种能杀灭病毒的什么素。这种懒人哲学,守株待兔,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人类是智能物种,有高度智能化的医药科学和制药工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一定要,也一定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主动,积极,有目的,有计划地智造出能够杀灭病毒的药物,最终战胜病毒这个更难对付的家伙。
笔者孤陋寡闻,但是从一种媒体上得知,美国国会和白宫已经拨款32亿美元的巨资开发口服的抗病毒药片。中国正在同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我们岂能不奋起直追,直至赶超!须知,我们在这方面大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医药这个宝库。屠呦呦们提炼出青蒿素,帮助人类战胜疟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后续待开发的宝贝多得很,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笔者上世纪中期以前出生在四川,那时在那个封闭的大盆地里面,可以说只有中药汤剂这一种药物。所以,我从小就喝汤药,终生信服汤药——当然,须是高明的中医师开具的方子。青年和中年时代困扰我的口疮,西医西药没有好办法,可是中医汤药总能治好。感冒之后的支气管炎咳嗽,其病原体有多种,按我的经验,一定要中西药同时用;因为抗生素可以杀灭细菌,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衣原体和支原体还能勉强对付,可是对付不了病毒,而中药对付得了。2020年武汉因新冠病毒肺炎封城期间,由天津中医院院长张伯礼负责的方舱医院,收治4000多病人,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或死亡,从电视上看,他们一直在用大坛子熬中药。从以上事例和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当中,我得出一个猜想:治疗由病毒引起的口疮、咳嗽和肺炎,一般都要用金银花(双花)、连翘、黄芩、板蓝根和大青叶这几味中药,治疗可能也是由病毒引起的慢性鼻炎(抗生素无效),一般都要用到苍耳子和木笔花(辛夷)。很可能,在这类“苦寒”中药材(双花不属于苦寒类)里面隐藏着能抑制甚至杀灭病毒的成分。
所以我呼吁,在当前这个人类同病毒大决战的关头,中国应当发挥自己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组成几个团队攻关,对这类中药材的成分做化学分析,找出上述几味中药材的共同成分——按我这个外行人的推测,上述几味中药材共同具有的成分,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抗病毒特效药;然后,再借鉴提炼青蒿素的方法,将那一种或几种成分提纯,制成药片或针剂,进一步再做临床试验。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各国一次又一次反复发作来看,靠疫苗终结大流行的愿景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落空,我们应当转换脑筋加紧研发特效药,这也可以说是“两条腿走路”吧。
事关重大,有1%的希望就应当做100%的努力。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的时刻到来了!
世界就是这样吊诡: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已经征服地球万物,正在不断征服大自然,并且一步步征服宇宙,可是,至今却还是拿最低级的生命体病毒没办法。办法是有,譬如打预防针,可不是很灵——打完还是可能被病毒侵害甚至致死;而且,预防针剂的创制很困难,生产过程很复杂,注射过程比较麻烦,因而推进得相当慢。
上文说病毒是“生命体”其实是抬举它了,准确地说,它是“半生命体”。因为,病毒是最原始的生命,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过渡形态。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只是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核酸(dna或rna),没有细胞质和细胞核,不能独立完成生命体的本质特征自复制;只有附着到寄生活细胞的细胞壁上,外壳上的蛋白质毒刺刺破寄生细胞的细胞壁,病毒将自己携带的dna或rna注入寄生细胞,借助寄生细胞的自复制机制,病毒才借尸还魂,开始自己的自复制,表现出生命体的本质特征。一旦离开寄生细胞,病毒单独存在的时候,它只是无生命的结晶体。病毒之所以难对付,可能正是因为它的这种无生命体和生命体的两面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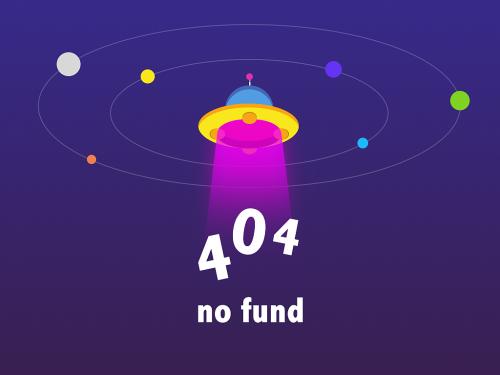
美国辉瑞药厂公布,新研发新冠病毒口服药物的二、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结果,发现成年患者在出现病征后3至5日内服药,重症住院或死亡机会率可以降低89%。美国药管局前局长兼现任辉瑞董事戈特利布也信心预言,美国冠病疫情有望在熬过德尔塔感染潮后,于明年1月初结束。
你看,短短一年半,新冠病毒已经传遍全球20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两亿,患病致死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可是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疫情……在许多国家仍然纷至沓来。需要说明的是,传染疱疹和乙肝之类传染病的是双链dna病毒,一条链发生变异,另一条链对变异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真正发生变异的几率很低;而传染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的是单链rna病毒,自身没有纠错复位机制,所以发生变异的几率很高。这就是新冠病毒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异的原因。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使用希腊字母命名新冠病毒变异株,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拉姆达……,一个比一个传染力更强,传染更快,传染更广,致死率更高。世卫组织近日又宣布,如果24个希腊字母不够用,要考虑用星座名称命名新冠毒株变体——须知宇宙中星座几乎是无限多呀!因此,人类似乎看不到这场瘟疫终结的希望在何处,终结的时间是何时。看来,人类同病毒决战的时刻真的到来了!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发新的检测手段、新的疫苗和新的药物。人类医学创新能力正在同新冠病毒变异能力赛跑,输赢胜败难说,其结果关乎人类未来命运!刚刚又读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警告说:“未来还可能出现人类根本对付不了的病毒!”此言绝非虚妄,也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真实的威胁。
这不由得令人回望过去几千年人类同上一个死敌细菌的抗争。在地球生命体的阶梯上,细菌比病毒高一个层级,是具有完整细胞结构并能独立复制的单细胞生命体。正因为能独立复制,致病细菌的传染力特别强。鼠疫、霍乱、痢疾、伤寒、脑膜炎、麻风病、白喉、炭疽、肺结核……都是细菌造成的恶性传染病,不知使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就拿排第一的鼠疫来说吧。从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欧亚大陆发生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夺走了大约一亿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其中。第二次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大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的这两句诗,用来描写黑死病肆虐的欧亚大陆是很恰当的。
那么,人类是怎样制伏细菌从而减少直至根绝这些传染病的呢?回答是:靠偶然性。
1928年,英国伦敦的一位医生弗莱明一直在研究对付葡萄球菌的办法。人们受伤后伤口化脓,多半是葡萄球菌感染。他在一只只培养皿里培养出葡萄球菌,然后试验用各种药剂去杀灭它们。他做这项工作已经好几年,仍然一无所获——这种葡萄球菌实在是个难对付的家伙!9月的一天早晨,弗莱明发现其中一只培养皿里竟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毛。这是因为他开着窗户,肉眼看不见的某种天然霉菌的孢子飞进来,落下去并繁殖起来了。显然,这只培养皿里的培养物被霉菌污染了。弗莱明正要把发了霉的培养物倒掉,突然心生一念:何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啊!”弗莱明大叫一声,马上激动起来:霉斑周围是清澈的,葡萄球菌被杀死了!这不正是梦寐以求的葡萄球菌的克星吗!
他立即动手大量培养这种青绿色的霉菌,将含有霉菌分泌物的培养液过滤,滴到葡萄球菌上去。结果,葡萄球菌全部被杀灭。弗莱明把这种培养液叫做青霉素。1929年6月,弗莱明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实验病理学》季刊上。可是,这篇论文竟未能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弗莱明本人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继续研究下去。直到1938年,英国医生佛罗理和钱恩在研究溶菌酶的时候,从检索的文献中发现了弗莱明的那篇文章,并立即着手继续弗莱明当年的研究。这样,青霉素才第二次被发现。佛罗理和钱恩将弗莱明发现的液状霉素加工,经过过滤、浓缩、提纯、干燥,终于得到了一种黄色粉末。1941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青霉素治病的临床试验,结果大获成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大批伤员急需高效抗菌药,在美国的帮助下,青霉素终于能大批量生产,成为一种价格便宜的抗菌特效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1945年,青霉素先后两次被发现的有功之臣——弗莱明、佛罗理、钱恩,一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此后,多种抗生素接连创制出来,人类终于战胜细菌。
有鉴于这个故事,我们似乎只能将战胜病毒的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面:一年,十年,百年,千年,万年……,瞎猫碰死耗子,某一天,又有一个人,碰巧发现一种能杀灭病毒的什么素。这种懒人哲学,守株待兔,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人类是智能物种,有高度智能化的医药科学和制药工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一定要,也一定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主动,积极,有目的,有计划地智造出能够杀灭病毒的药物,最终战胜病毒这个更难对付的家伙。
笔者孤陋寡闻,但是从一种媒体上得知,美国国会和白宫已经拨款32亿美元的巨资开发口服的抗病毒药片。中国正在同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我们岂能不奋起直追,直至赶超!须知,我们在这方面大有优势,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医药这个宝库。屠呦呦们提炼出青蒿素,帮助人类战胜疟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只是开了一个好头,后续待开发的宝贝多得很,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笔者上世纪中期以前出生在四川,那时在那个封闭的大盆地里面,可以说只有中药汤剂这一种药物。所以,我从小就喝汤药,终生信服汤药——当然,须是高明的中医师开具的方子。青年和中年时代困扰我的口疮,西医西药没有好办法,可是中医汤药总能治好。感冒之后的支气管炎咳嗽,其病原体有多种,按我的经验,一定要中西药同时用;因为抗生素可以杀灭细菌,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衣原体和支原体还能勉强对付,可是对付不了病毒,而中药对付得了。2020年武汉因新冠病毒肺炎封城期间,由天津中医院院长张伯礼负责的方舱医院,收治4000多病人,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或死亡,从电视上看,他们一直在用大坛子熬中药。从以上事例和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当中,我得出一个猜想:治疗由病毒引起的口疮、咳嗽和肺炎,一般都要用金银花(双花)、连翘、黄芩、板蓝根和大青叶这几味中药,治疗可能也是由病毒引起的慢性鼻炎(抗生素无效),一般都要用到苍耳子和木笔花(辛夷)。很可能,在这类“苦寒”中药材(双花不属于苦寒类)里面隐藏着能抑制甚至杀灭病毒的成分。
所以我呼吁,在当前这个人类同病毒大决战的关头,中国应当发挥自己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组成几个团队攻关,对这类中药材的成分做化学分析,找出上述几味中药材的共同成分——按我这个外行人的推测,上述几味中药材共同具有的成分,很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抗病毒特效药;然后,再借鉴提炼青蒿素的方法,将那一种或几种成分提纯,制成药片或针剂,进一步再做临床试验。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各国一次又一次反复发作来看,靠疫苗终结大流行的愿景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落空,我们应当转换脑筋加紧研发特效药,这也可以说是“两条腿走路”吧。
事关重大,有1%的希望就应当做100%的努力。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的时刻到来了!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