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
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
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

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皚皚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
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此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
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入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
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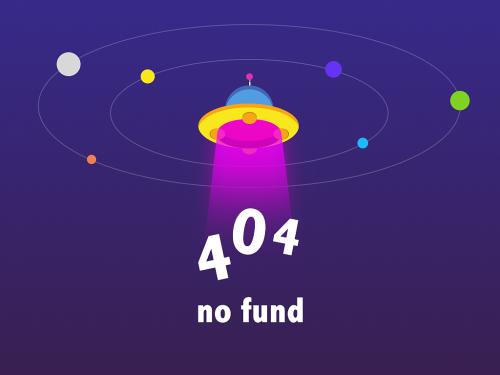
托尔斯泰
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却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
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
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

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
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皚皚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
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此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
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入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
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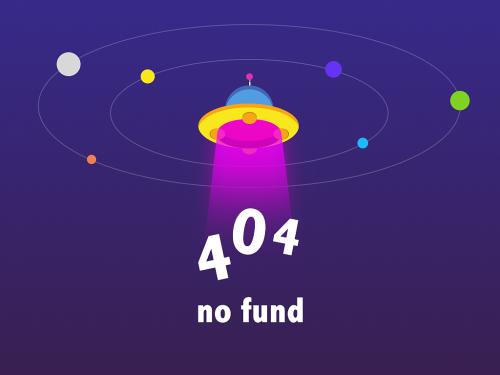
托尔斯泰
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却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