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不久,不少人认为中国供应链将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外流时,刚刚出版《溢出》一书的青年学者施展根据他对于海外供应链的研究,做出了相反的判断。
而在今年一片看好中国gdp总量即将提前超过美国的乐观声音中,施展又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美国创新高度相关,但中美在创新层面有很大区别,美国更多是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是从1到n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不一样,在短期内恐怕还很难改变,这让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在2020年底,施展又推出了新著《破茧》。在这本书中,施展重点关注了当代社会的“信息茧房”问题及如何破解之上。《巴伦周刊》近期采访了施展,与他一起回顾了年初他对于中国供应链转移问题的判断,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解读,以及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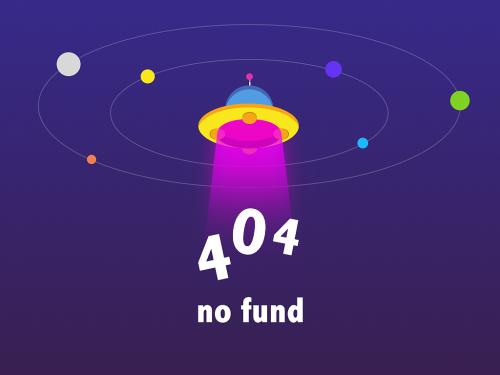
《巴伦周刊》:我们先回顾一下去年年初的采访。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不久,您对于中国供应链是否会向海外转移做出了跟不少经济学家相反的判断,事实证明您的判断更加符合现实:中国供应链不但没有大规模流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回流,比如近期的印度纺织业,那么您如何回看当初的这个判断?
施展:有些经济学者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对中国前景极度悲观,认为国内近年来对自身供应链枢纽的地位过分高估,海外资本通过疫情机会在进行压力测试,测试排除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当时我对疫情下的中国经济持谨慎悲观的态度。
之所以悲观,毕竟当时的形势非常糟糕,谁也没法太乐观;但我认为,除非疫情仅局限于中国,并且持续好几年,否则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仍然不会受到实质性冲击,因为我在《枢纽》、《溢出》两本书中提出的中国经济成长逻辑的一些基本条件,都还没有发生逆转。所以当时我的“悲观”也是“谨慎”的。
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又作出了极度乐观的预测,认为2018年贸易战以来美国自损式的极限施压政策彻底失效,今年新冠疫情影响之下中美两国经济一升一降,叠加上人民币升值,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75%,甚至认为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可以超越美国,到2049年美国经济体量可能反过来是中国的75%。
这些学者前后两个极端的判断都让我有点吃惊。现在,我仍要提出跟这类观点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认为美国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策略。如果说一部分人在疫情刚开始时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如今又过于乐观,而我在当时是谨慎悲观,现在则是谨慎乐观。
乐观在于,我始终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不出现技术的实质性跃迁的前提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在整体上没有太大问题。在具体的微观企业层面,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微观层面的问题并不会线性传导到整体的宏观状态上。因为宏观状态是由大系统、大网络来决定的,并不是由具体某个微观企业决定的,除非这个企业是整个网络中极度重要的节点。
举例来说,即使华为撑不过美国的制裁,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中国的通信行业没有希望了。个别企业受到了巨大压力,但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都还在中国,华为的人才可以出来创业,又会有许多新的科技企业冒出来,所以从系统上来看,宏观问题不大。
有的学者在2020年2月初说,当时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但美股一片火热,这证明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动性不强。我当时在接受《巴伦周刊》采访时就反驳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月初美股就经历了历史性的连续熔断,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美股熔断是因为中国的影响。中美经济联动性当然很强,但它不是简单的线性传导关系。
在当前中美疫情冰火两重天的语境下,过分乐观的学者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在2035年超越美国,甚至美国经济总量在2049年是中国的75%,我认为,即便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多大意义。
原因在于,讨论国家实力的时候,gdp是个重要指标,但如果仅仅拿gdp这个统计指标来讨论问题,那就太离谱了。看世界经济史的一些统计数据,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大清的gdp是英国的很多倍,甚至一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一,之后才跌落下来,可是如果不去看经济的内部结构,以及各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结构性位置,这种gdp的第一有多大意义呢?研究者如果仅仅痴迷于这些数字的话,我认为是很不严谨的。

图 | 1960-2020中美gdp走势
过分乐观的学者看低美国,大概是因为看到现在美国社会撕裂十分严重,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但我们要进一步看到,这种社会撕裂与中美两国间经济的结构性关系相关。
我在近年出版的几本书中都谈到了,中美经济存在一个高度联动的关系,简要来说这个关系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之前接受您采访的时候我也提到过,一个在硅谷做投资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判断一个新技术是否值得投资的依据之一,就是看该公司在中国深圳有没有办公室,如果没有,风投就无法相信你的创新能够大规模快速落地。这个例子就很好地体现了美国的创新跟中国的生产之间的深度联动关系。
不过我们必须还要看到,美国的创新与中国的生产的深度联动,旁边还有个落寞的第三方,就是美国的传统产业。美国的创新产业与美国的传统产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甚至小于它与中国生产部门的关联度,这就导致了创新产业当中的人群与传统产业当中的人群的撕裂关系,导致美国严重的社会撕裂。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可以说中美关系根本不是个双边关系,而是三边关系,是“美国创新部门—中国生产部门—美国传统部门”所对应的三种人群下的三边关系,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困境,是需要在这个三边关系下才能恰当理解的。
不过仅从美国的创新部门与中国生产部门的联动关系下来观察,会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跟美国创新之间虽然不是严格的线性传导关系,但确实是也高度相关的。这里面有着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重要的结构性关系,是比gdp的那些数字更值得关注的。
01、想要突破内卷困境,就必须进入“从0到1”
《巴伦周刊》: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看中美经济一升一降,长远来说,美国创新乏力也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
施展:是的。我在三年前出版的《枢纽》一书中就在谈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高速增长,是和美国9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这一轮创新经济的特性直接相关的。美国的这一轮创新经济要求大规模外包,作为外包的承包方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特殊条件,而中国刚好因为一系列历史机缘的时间耦合,满足了这些特殊条件,于是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包承接方,在美国创新经济的拉动下,获得了迅猛的崛起。具体的逻辑我在近年出版的这三本书里有细致论证,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看到,中国最近也在努力推动自主创新,但中美在创新层面有很大区别,美国更多是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是从1到n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于从1到n的创新来说,所需要的条件是大规模的组织能力,以及超大规模市场。而这两个方面,中国目前有较大优势,所以中国在从1到n的创新上非常强。从1到n的创新带来的就大规模量产能力,这种能力会带来很好的财富扩散效应,从而,从1到n的创新可以迅速地把整个社会都给调动起来。但是这种创新它仅仅是量的扩展,不是质的跃迁;当量逐渐扩展到把整个现有市场都填满了之后,还想要继续扩展的话,就会走向内卷。
《巴伦周刊》:要想突破内卷困境,就必须进入到从0到1的创新领域?
施展:是的,可是想要进入到从0到1的创新,所需要的条件和从1到n的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前者所需要的更多地是一种制度条件,它需要有自由的研究空间,需要能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制度环境,需要有在全球范围开展深度、密切的学术交流的条件,还需要极为扎实的基础研究。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厉害,中国孩子的奥数很厉害,但真正的数学跟奥数有着巨大区别,扎实的基础教育并不能线性传导地形成扎实的基础研究。
刚说的所有这些条件,要想能够具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在这方面,今天的中国跟美国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可预见未来,美国在从0到1的创新上仍然是独步天下的。
但是,从0到1的创新尽管能带来质的突破,却无法带来财富的扩散。这就会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在实现0到1的创新之后,它需要通过中国完成从1到n的过程,也就是说财富的扩散在中国,而美国只有少数人、产业和地区享受了0到1所带来的财富汇聚。
结果就是前面刚刚说过的,美国的传统产业在走向衰落,但是美国东西海岸的创新产业和金融业跟中国之间有高度捆绑的利益联动关系。甚至可以说,美国从0到1的创新能力越强,美国社会的内在撕裂就越大,创新产业赚得越盆满钵满,传统产业就陷入越深的困境。这就导致了前面说的那种三边关系,导致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撕裂。
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认为,在未来十年,虽然从微观上看,中国经济会有各种糟糕的事情,但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经济都不会出太大问题,除非这期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技术跃迁。
再看美国,到了2030年或者2035年,美国可能会重新从今天的社会撕裂再走向统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说的美国传统部门里面的劳动者,他们因为机器人或者中国劳动力的替代而失业了,这种失业来得太快,失业者的技能只适用于传统产业,无法让他们进入到美国的新产业当中,于是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到2035年,如今的失业人群已经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而在这十五年中,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都是与美国当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相关的,也就是从0到1的创新部门,以及与其能够联动起来的各种衍生部门,美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化掉了。现在的美国正处于自身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阵痛期,如果有谁说美国这就不行了,那看得可能就有些短了。
《巴伦周刊》:您是说通过一代人的自然更替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施展:对,非常不精确地说,这一代人的自然更替到2035年是会完成的。当然,你总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微观个案来反驳,但从宏观上来说,到那个时候,这个更替是能够大致完成的。一旦这个更替完成,目前中美关系的三边关系状态,就会重新回到双边关系。
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仍会逐渐释放它从0到1的强大创新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相当强的联动性,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经济突破内卷的机会,仍然在于与美国的创新产业之间的联动关系。
不考虑分配问题,仅仅从资本增值的效率上看,从0到1的创新会比从1到n的创新更快地积累财富,所以仅从gdp总量来看,我并不像有些人那么乐观地认为到2035中美经济会拉平,因为我们不能脱离开美国的增长来谈论中国的增长。更何况,就算拉平了,那又怎样?重要的是结构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只能是一种谨慎乐观。
《巴伦周刊》:两个国家gdp的测量与对比本来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哪怕我们总量上真的追上了美国,人均水平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对比更多是象征性的。
施展:的确,象征性意义更大。我再补充一点,中美的经济逻辑还在进一步演化,可能到十几年后,美国从0到1的能力更强了,而中国从1到n的能力也更强了,但那时候的经济逻辑跟今天也会不一样,很多理论框架也需要调整、发展。
统计gdp的时候需要一系列数据指标,但任何数据都需要在一整套的理论框架当中才能获得意义的,脱离开理论框架的赤裸数据没有任何意义,你从中解读不出东西来的。所以,用今天的理论框架来讨论到那个时候的gdp对比,我真的不认为这种讨论有多大意义。
02、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巴伦周刊》:新冠疫情让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随后控制得比较好,但欧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在您的预期之中吗?
施展: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倒不是对中国控制疫情比较好感到意外,我是对西方控制疫情如此差感到比较意外。
疫情爆发后,我在公号上发过一篇“施展札记”提出,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病毒的出现是个自然现象,没有人需要为病毒在何处出现负责,因为没人能控制它,但是病毒在出现后是否扩散为疫情,这就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
从这个维度上理解,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的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全能型政府,这包含了一个隐含逻辑,即它必须是全善的,若不全善,则没资格全能。
而能否控制住疫情,是评价我们的政体是否全善的一个指标,因此全能型政府为了自身的正当性,必须和疫情势不两立,这是由它的正当性逻辑决定的。
全能型政府必须全善,这就意味着它对于社会有一种兜底性承诺。而西方政体对社会没有兜底性承诺,这意味着疫情即便扩散开,也不伤及它的政治正当性。所以在西方,跟疫情可以是一个共存关系。
虽然这种共存关系虽然不会伤及政体的正当性,但并不代表着因此就可以放任疫情扩散。然而,西方的政体逻辑是基于其人权理念,这种逻辑就使得政府在疫情的极端状态下,要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制,比如像中国一样进行高效率的禁足,有着很高的政治决策成本,很难做到。
中国政府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政府给了百姓兜底性承诺,某种意义上,百姓的责任是被政府给接盘了,与之相对应,百姓的权利也被政府接盘,因为权和责一定是对应的。政府接盘百姓的责任之后,它就有权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禁足。中国可以做到,有几个病例就对一大片地区的民众进行隔离。中国既有这种组织力,同时又不伤害正当性。但是在西方做不到,因为这既会伤害它的正当性,它也没有这种高效的组织力。
但这些刚才说的这些都与制度优势或者劣势什么的没有关系,我称之为这是一个“制度特性”或“制度效果”。禁足会不会伤害政体的正当性,这是一个制度特性;无法有效禁足,会影响控制疫情的能力,这是制度效果。但这些都无法直接转换为对制度的优势或劣势的判断。
特性或效果是一个事实判断,优势或劣势是一个价值判断。现在国内的讨论当中经常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同,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
《巴伦周刊》:中国疫情防控较好,复工复产较快,货币政策保留空间较大,人民币也保持强势。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判断变得特别乐观,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施展:整体上我确实看好中国经济,但我也要强调,这跟制度优劣势无关,我做的仅仅是个事实判断,并不关乎任何价值判断。我的看好,指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5到10年内不会遭遇实质性的问题,除非又出现一个我们今天完全意想不到的巨大黑天鹅事件。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内,我不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会遭遇会到什么问题。
但随着时间拖长,gdp统计的意涵会改变,仅仅基于数值来说中国的经济前景,意义不大,必须看经济的结构。要看你在忙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你是每天忙着搬砖,还是每天忙着码字?虽然都很忙,但不同的忙活,在社会上的结构性位置、议价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03、平台型企业具有社会公共品的性质
《巴伦周刊》:疫情除了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很大变化,还在企业领域带来了更强的马太效应,比如说全球的互联网巨头和平台型公司都逆势发展,越小的企业可能受损越严重,这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反弹,您能说说对互联网产业反垄断的看法吗?
施展:首先,怎么定义垄断就是个问题。我在《破茧》这本书里面引用了一本书叫做《激进市场》,那里面就谈到垄断。比如你要去买房子,没有哪两个房子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单元门里的房子,不同的楼层,它的采光也不一样。
所以你买下某一个房子,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样的东西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对这个独一无二的房子就垄断了,只要是垄断就会有租的存在。要是把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追到极端,那么除了大宗商品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均质化的,只要非均质化,就存在垄断,就存在租。《激进市场》里就此衍生出一系列极富想象力的讨论,在这就不展开了,继续咱们的话题。
咱们这话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不用蚂蚁金服,我仍然可以用微信支付。我在社交软件上不用微信,也可以用钉钉,还可以用飞书,可以用whatsup,我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在企业试图基于垄断地位对我进行控制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它,另找一个东西来替代。实际上没有什么产品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它真的构成垄断吗?
刚才这俩例子,从两个比较极端的方向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觉得有垄断的地方,可能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我们觉得有垄断的地方,似乎它也未必真的是垄断。到底什么是垄断?这个问题,学界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观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没有统一的观点。所以反垄断究竟效果会怎样,这一点我也是很谨慎的。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也在流传张维迎教授的一篇演讲,里面谈到垄断分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准入制的,不经批准你就不能进来;而市场性垄断,是我干得比你好,但是我没有准入制,你进不来是因为你没我干得好。我为了维持垄断地位,仍然要不断提升我的服务,否则我就被人替代了。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混在一起来看。对于市场性垄断的反垄断效果,我是很谨慎的。
不过,看这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我认为现在监管蚂蚁金服这类的企业,不能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马云说中国根本还没有金融系统,所以何来系统性金融风险?我能明白马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当然有系统,蚂蚁本身就构成一个系统了。哪怕你是个私营企业,只要你的规模足够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从产权上来说你仍然是个私营企业,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你就不再仅仅是私营企业了,你开始成为公共品,也就相应地必须承担起大量的社会责任,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盈利的责任了。
这样的巨头,作为公共平台,就不能完全用商业标准来做评判。可能有人会反对我的这个说法,说这是让商人背上不应有的包袱,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中小商人,我会同意这种批评,但如果讨论的是巨头平台,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更容易说明白这问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书中提出,当时法国和意大利在凡尔赛和约中要向德国压榨极大数额的赔款。为什么呢?除了民族主义激情的冲动外,还有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和意大利都欠了英国和美国大量的战债,而为了能够还得起债,它们就只得从德国那里榨钱。
在这种情况下,英美该怎么做呢?凯恩斯说英美就应该主动放弃这些战债。按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凭什么要人放弃战债呢?关键是战争贷款跟商业贷款完全不是一回事,商业贷款当然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战争贷款是一笔政治贷款,政治贷款意味着,你是否要收回这笔贷款,判断标准是,收款这件事情是否符合你最初发放这笔贷款时的政治目的。
如果收这笔贷款所带来的政治效果,会跟你最初的政治目的正好相反——也就是很可能带来下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此时你就应当放弃这笔贷款。但也不能要求英美白白放弃战债,它们应该牵头成立一个超越于各国之上的国际经济组织,以此来克服各国的民族主义激情在全球经济中会带来的巨大问题,而法国、意大利等欠了战债的国家,则应该接受英美在这个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主导地位。
从这个例子再回到刚才我说的监管蚂蚁金服这个问题上。从商业意义上,反垄断是否有正当性?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学界对这个事也没有共识。但是企业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平台之后,成为了社会公共品,就有了巨大的社会责任,对这社会责任就不能用商业标准来判断了。所以从社会责任是否履行到位的意义上来说,对蚂蚁金服进行有效的监管,我是认同的,但这种意义上的监管和反垄断是不同的两回事。而蚂蚁一方面应当接受社会责任意义上的监管,同时因为它在提供新式的公共品,也应当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向蚂蚁释放出来,这才是公平的,也会激励更多企业担当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我在书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但是说得比较简略,很多人可能看的时候一带而过,因为那个概念也是大多人都不熟悉的,就是隐私计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现在正在发展起来。
现在互联网巨头的做法都是搜集用户数据上传到自己的云服务器上,然后在平台上用算法处理,给用户推送相应内容。数据上传经过算法的处理后,基本消费者对企业就是透明的了,隐私都被企业拿走了。
但隐私计算的玩法是,数据不上传,算法下传,算完了的结果再上传。而下传的算法在消费者终端上进行运算的时候,数据是什么,算了多少次,等等内容全都是加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就是说这些隐私仍然在用户自己的手上。同时,隐私算法还能保证消费者仍然可以享有现在互联网的所有便利。
比如在现实生活当中您有个真实身份,在网上您又有一个虚拟的身份叫阿龙,这个虚拟身份实际上就对应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同时也是你的数字钱包。你所有的数据都是以阿龙这个虚拟身份或说账号为载体而生成的,隐私计算可以保证,一方面,人们无法把阿龙对应到您的肉身上,另一方面,阿龙背后又有一个可被验证的真实存在,也就是一个匿名的真人,信用是真实的,各种交易也是可以放心展开的。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巨头可以根据阿龙这个账号的喜好来给他推荐相应的内容,账号的所有者仍然拥有过去的便利,却并不把自己的隐私向平台敞开。而平台去推送这些消息或内容的时候,实际上卖广告的过程就可以展开了,阿龙还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分红。
04、隐私计算、信息茧房与养蛊自噬
《巴伦周刊》:您说的这种前景当然很美好,但是比如说我们在疫情中间看到可能是网络身份和个人身份已经绑定得越来越紧了。
施展:隐私计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政府是没有动力去采用隐私计算的,因为它就掌握不了数据了嘛。但这不是政府想不想采用的事儿,有另外一个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往那个方向转型。
那是什么压力呢?最近一个信息可能你也注意到了,就是google前一段时间宕机了,而且这不是它第一次宕机了,最近这几个月google接连宕机。为什么会宕机呀?因为储存的数据太多了,它的服务器受不了了。连google都受不了了,可以想见别的公司会更快受不了。
随着5g、物联网的到来,连接到网络上的节点数会成数量级地增多,节点间发生各种交互,上传的数据量会是几何级数乃至指数级数地增长,到那会儿所有公司的服务器全都会受不了,没有任何一家云服务商能够受得了那种数据量。到那时,隐私计算就不得不采用办法了,因为它需要传递的信息量要小太多了。
《巴伦周刊》:您的意思是说,企业会因为成本收益的考虑主动放弃把用户的数据占为己有?
施展: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巨头们会放弃把数据上传,选择用算法下传,然后在各家都在这么做的时候,它们又会开始比拼一个新的东西,你在下传的时候我也在下传,同时我可以明确告诉用户,我的下传算法是隐私算法,什么叫隐私算法?你的数据里面的具体内容我全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阿龙,我完全对应不上真人。那么用户肯定都被我吸引走了,因为他们的隐私得到了我的尊重和保护嘛,这种情况下,就没别的企业事了。
而且我肯定不是空口说的,我的算法和代码都可以公开——现在不少企业都在这么做——任何人都可以来查一查,看我是否真的是隐私算法,看我有没有撒谎。那么一旦到了这一步,你会发现用户都被我给吸引走了,你就不得不也采用隐私算法,就会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
《巴伦周刊》:您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判断一直是比较分开的,但在2020年之后,这两者似乎被捆绑得更紧了。您觉得企业真的能实现“去国家化”吗?
施展:这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这些企业现在全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任正非是很反对用民族情结来绑架华为的,在去年舆论中,华为要有点抗美援朝中上甘岭的味道了,任正非马上就在内部说,我们不要用民族情绪来绑架自己,这会伤及我们自身。大的企业家没有谁想被这么绑架,这会让企业陷入莫名其妙的困境当中。
再看美国,google和facebook,同样不想被国家情绪所绑架。现在欧盟出台了一个新规,号称史上最严的数字管理规则。最头疼的肯定不是tiktok,而是facebook,facebook在欧洲的业务的比字节跳动大多了。所以这些巨头都有摆脱国家的约束,中立于国家之外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如何最终能够落实,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个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站在它们的立场上,你会发现,民族主义情绪越高涨越是绑架它们,它们就会产生越强的中立化需求。一个企业被民族主义绑架,结果就是它无法成为全球企业,只能作为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性企业。你要想成为全球性企业,必须得别的国家愿意让你进去,而别的国家愿意让你进去,前提是你不能携带一系列的民族主义情绪进来,所以越是全球化的企业,越有让自己中立性的需求。
只不过这个需求最终怎么实现,这些企业家们未必想得清楚,需要有更多人一块来想这个问题。我在《破茧》一书的整个第三部分都是在谈这个问题,所有那些讨论实际上都只是尝试打开脑洞,尝试用我这本书作为靶子,把问题提出来,吸引更多人一块来讨论这个问题。
《巴伦周刊》:这本书书名是《破茧》,但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似乎还是没有回答信息茧房到底应该怎么破解?
施展:实际上我在书里面已经写到了,但出版后我在反思时,意识到我没有写清楚。我提到了,信息茧房可能需要某些公共事件才能被打破,借助一个公共事件来把所有人的茧房都给冲开,把墙壁冲碎,但这只是破坏性的,还不是建设性的。
建设性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的信息茧房,它的一个很重要成因在于推荐算法,推荐算法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模式,只要是好的商业模式,用政策控制是控制不住的,但是信息茧房也会给使用它的公司带来一系列反噬效应。
比如像字节跳动,它是推荐算法应用得非常到位的一个企业。但是今天它也遭遇到反噬了,因为推荐算法强化了信息茧房,而在信息茧房下,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这就像养蛊一样,这些被信息茧房培育出来的民族主义,最终反噬了字节跳动,让字节在面对美国巨大压力的时候,它的言论空间、决策空间反倒被大幅压缩了,它被民族主义所绑架了。这些绑架它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一部分就是它的信息茧房给喂养出来的。
在未来,企业逐渐都会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反噬效应,推荐算法本身很可能会演化出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要保证不会把人给困在信息茧房里面,这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善良,而是因为这样才符合它们的利益。如果推荐算法在今天会让这些企业养蛊自噬,那么在这种恐惧下,一种新的商业伦理就可能会浮现出来。未来突破信息茧房突破的前景就在此。
《巴伦周刊》:谢谢您。
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不久,不少人认为中国供应链将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外流时,刚刚出版《溢出》一书的青年学者施展根据他对于海外供应链的研究,做出了相反的判断。
而在今年一片看好中国gdp总量即将提前超过美国的乐观声音中,施展又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美国创新高度相关,但中美在创新层面有很大区别,美国更多是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是从1到n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不一样,在短期内恐怕还很难改变,这让他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在2020年底,施展又推出了新著《破茧》。在这本书中,施展重点关注了当代社会的“信息茧房”问题及如何破解之上。《巴伦周刊》近期采访了施展,与他一起回顾了年初他对于中国供应链转移问题的判断,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解读,以及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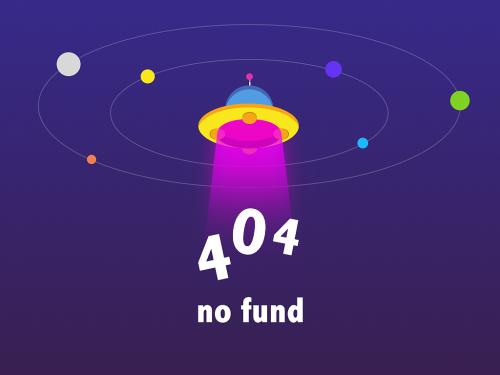
《巴伦周刊》:我们先回顾一下去年年初的采访。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不久,您对于中国供应链是否会向海外转移做出了跟不少经济学家相反的判断,事实证明您的判断更加符合现实:中国供应链不但没有大规模流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回流,比如近期的印度纺织业,那么您如何回看当初的这个判断?
施展:有些经济学者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对中国前景极度悲观,认为国内近年来对自身供应链枢纽的地位过分高估,海外资本通过疫情机会在进行压力测试,测试排除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当时我对疫情下的中国经济持谨慎悲观的态度。
之所以悲观,毕竟当时的形势非常糟糕,谁也没法太乐观;但我认为,除非疫情仅局限于中国,并且持续好几年,否则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仍然不会受到实质性冲击,因为我在《枢纽》、《溢出》两本书中提出的中国经济成长逻辑的一些基本条件,都还没有发生逆转。所以当时我的“悲观”也是“谨慎”的。
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又作出了极度乐观的预测,认为2018年贸易战以来美国自损式的极限施压政策彻底失效,今年新冠疫情影响之下中美两国经济一升一降,叠加上人民币升值,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75%,甚至认为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可以超越美国,到2049年美国经济体量可能反过来是中国的75%。
这些学者前后两个极端的判断都让我有点吃惊。现在,我仍要提出跟这类观点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认为美国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策略。如果说一部分人在疫情刚开始时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如今又过于乐观,而我在当时是谨慎悲观,现在则是谨慎乐观。
乐观在于,我始终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不出现技术的实质性跃迁的前提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在整体上没有太大问题。在具体的微观企业层面,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微观层面的问题并不会线性传导到整体的宏观状态上。因为宏观状态是由大系统、大网络来决定的,并不是由具体某个微观企业决定的,除非这个企业是整个网络中极度重要的节点。
举例来说,即使华为撑不过美国的制裁,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中国的通信行业没有希望了。个别企业受到了巨大压力,但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都还在中国,华为的人才可以出来创业,又会有许多新的科技企业冒出来,所以从系统上来看,宏观问题不大。
有的学者在2020年2月初说,当时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但美股一片火热,这证明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动性不强。我当时在接受《巴伦周刊》采访时就反驳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月初美股就经历了历史性的连续熔断,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美股熔断是因为中国的影响。中美经济联动性当然很强,但它不是简单的线性传导关系。
在当前中美疫情冰火两重天的语境下,过分乐观的学者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在2035年超越美国,甚至美国经济总量在2049年是中国的75%,我认为,即便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多大意义。
原因在于,讨论国家实力的时候,gdp是个重要指标,但如果仅仅拿gdp这个统计指标来讨论问题,那就太离谱了。看世界经济史的一些统计数据,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大清的gdp是英国的很多倍,甚至一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一,之后才跌落下来,可是如果不去看经济的内部结构,以及各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结构性位置,这种gdp的第一有多大意义呢?研究者如果仅仅痴迷于这些数字的话,我认为是很不严谨的。

图 | 1960-2020中美gdp走势
过分乐观的学者看低美国,大概是因为看到现在美国社会撕裂十分严重,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但我们要进一步看到,这种社会撕裂与中美两国间经济的结构性关系相关。
我在近年出版的几本书中都谈到了,中美经济存在一个高度联动的关系,简要来说这个关系就是: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之前接受您采访的时候我也提到过,一个在硅谷做投资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判断一个新技术是否值得投资的依据之一,就是看该公司在中国深圳有没有办公室,如果没有,风投就无法相信你的创新能够大规模快速落地。这个例子就很好地体现了美国的创新跟中国的生产之间的深度联动关系。
不过我们必须还要看到,美国的创新与中国的生产的深度联动,旁边还有个落寞的第三方,就是美国的传统产业。美国的创新产业与美国的传统产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甚至小于它与中国生产部门的关联度,这就导致了创新产业当中的人群与传统产业当中的人群的撕裂关系,导致美国严重的社会撕裂。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可以说中美关系根本不是个双边关系,而是三边关系,是“美国创新部门—中国生产部门—美国传统部门”所对应的三种人群下的三边关系,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困境,是需要在这个三边关系下才能恰当理解的。
不过仅从美国的创新部门与中国生产部门的联动关系下来观察,会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跟美国创新之间虽然不是严格的线性传导关系,但确实是也高度相关的。这里面有着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重要的结构性关系,是比gdp的那些数字更值得关注的。
01、想要突破内卷困境,就必须进入“从0到1”
《巴伦周刊》: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看中美经济一升一降,长远来说,美国创新乏力也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
施展:是的。我在三年前出版的《枢纽》一书中就在谈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高速增长,是和美国9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这一轮创新经济的特性直接相关的。美国的这一轮创新经济要求大规模外包,作为外包的承包方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特殊条件,而中国刚好因为一系列历史机缘的时间耦合,满足了这些特殊条件,于是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包承接方,在美国创新经济的拉动下,获得了迅猛的崛起。具体的逻辑我在近年出版的这三本书里有细致论证,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看到,中国最近也在努力推动自主创新,但中美在创新层面有很大区别,美国更多是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是从1到n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于从1到n的创新来说,所需要的条件是大规模的组织能力,以及超大规模市场。而这两个方面,中国目前有较大优势,所以中国在从1到n的创新上非常强。从1到n的创新带来的就大规模量产能力,这种能力会带来很好的财富扩散效应,从而,从1到n的创新可以迅速地把整个社会都给调动起来。但是这种创新它仅仅是量的扩展,不是质的跃迁;当量逐渐扩展到把整个现有市场都填满了之后,还想要继续扩展的话,就会走向内卷。
《巴伦周刊》:要想突破内卷困境,就必须进入到从0到1的创新领域?
施展:是的,可是想要进入到从0到1的创新,所需要的条件和从1到n的创新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前者所需要的更多地是一种制度条件,它需要有自由的研究空间,需要能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制度环境,需要有在全球范围开展深度、密切的学术交流的条件,还需要极为扎实的基础研究。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厉害,中国孩子的奥数很厉害,但真正的数学跟奥数有着巨大区别,扎实的基础教育并不能线性传导地形成扎实的基础研究。
刚说的所有这些条件,要想能够具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在这方面,今天的中国跟美国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可预见未来,美国在从0到1的创新上仍然是独步天下的。
但是,从0到1的创新尽管能带来质的突破,却无法带来财富的扩散。这就会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在实现0到1的创新之后,它需要通过中国完成从1到n的过程,也就是说财富的扩散在中国,而美国只有少数人、产业和地区享受了0到1所带来的财富汇聚。
结果就是前面刚刚说过的,美国的传统产业在走向衰落,但是美国东西海岸的创新产业和金融业跟中国之间有高度捆绑的利益联动关系。甚至可以说,美国从0到1的创新能力越强,美国社会的内在撕裂就越大,创新产业赚得越盆满钵满,传统产业就陷入越深的困境。这就导致了前面说的那种三边关系,导致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社会撕裂。
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认为,在未来十年,虽然从微观上看,中国经济会有各种糟糕的事情,但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经济都不会出太大问题,除非这期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技术跃迁。
再看美国,到了2030年或者2035年,美国可能会重新从今天的社会撕裂再走向统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说的美国传统部门里面的劳动者,他们因为机器人或者中国劳动力的替代而失业了,这种失业来得太快,失业者的技能只适用于传统产业,无法让他们进入到美国的新产业当中,于是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到2035年,如今的失业人群已经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而在这十五年中,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都是与美国当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相关的,也就是从0到1的创新部门,以及与其能够联动起来的各种衍生部门,美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化掉了。现在的美国正处于自身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阵痛期,如果有谁说美国这就不行了,那看得可能就有些短了。
《巴伦周刊》:您是说通过一代人的自然更替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施展:对,非常不精确地说,这一代人的自然更替到2035年是会完成的。当然,你总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微观个案来反驳,但从宏观上来说,到那个时候,这个更替是能够大致完成的。一旦这个更替完成,目前中美关系的三边关系状态,就会重新回到双边关系。
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仍会逐渐释放它从0到1的强大创新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相当强的联动性,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经济突破内卷的机会,仍然在于与美国的创新产业之间的联动关系。
不考虑分配问题,仅仅从资本增值的效率上看,从0到1的创新会比从1到n的创新更快地积累财富,所以仅从gdp总量来看,我并不像有些人那么乐观地认为到2035中美经济会拉平,因为我们不能脱离开美国的增长来谈论中国的增长。更何况,就算拉平了,那又怎样?重要的是结构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只能是一种谨慎乐观。
《巴伦周刊》:两个国家gdp的测量与对比本来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哪怕我们总量上真的追上了美国,人均水平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对比更多是象征性的。
施展:的确,象征性意义更大。我再补充一点,中美的经济逻辑还在进一步演化,可能到十几年后,美国从0到1的能力更强了,而中国从1到n的能力也更强了,但那时候的经济逻辑跟今天也会不一样,很多理论框架也需要调整、发展。
统计gdp的时候需要一系列数据指标,但任何数据都需要在一整套的理论框架当中才能获得意义的,脱离开理论框架的赤裸数据没有任何意义,你从中解读不出东西来的。所以,用今天的理论框架来讨论到那个时候的gdp对比,我真的不认为这种讨论有多大意义。
02、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巴伦周刊》:新冠疫情让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随后控制得比较好,但欧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在您的预期之中吗?
施展: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倒不是对中国控制疫情比较好感到意外,我是对西方控制疫情如此差感到比较意外。
疫情爆发后,我在公号上发过一篇“施展札记”提出,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病毒的出现是个自然现象,没有人需要为病毒在何处出现负责,因为没人能控制它,但是病毒在出现后是否扩散为疫情,这就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
从这个维度上理解,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的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全能型政府,这包含了一个隐含逻辑,即它必须是全善的,若不全善,则没资格全能。
而能否控制住疫情,是评价我们的政体是否全善的一个指标,因此全能型政府为了自身的正当性,必须和疫情势不两立,这是由它的正当性逻辑决定的。
全能型政府必须全善,这就意味着它对于社会有一种兜底性承诺。而西方政体对社会没有兜底性承诺,这意味着疫情即便扩散开,也不伤及它的政治正当性。所以在西方,跟疫情可以是一个共存关系。
虽然这种共存关系虽然不会伤及政体的正当性,但并不代表着因此就可以放任疫情扩散。然而,西方的政体逻辑是基于其人权理念,这种逻辑就使得政府在疫情的极端状态下,要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制,比如像中国一样进行高效率的禁足,有着很高的政治决策成本,很难做到。
中国政府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政府给了百姓兜底性承诺,某种意义上,百姓的责任是被政府给接盘了,与之相对应,百姓的权利也被政府接盘,因为权和责一定是对应的。政府接盘百姓的责任之后,它就有权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禁足。中国可以做到,有几个病例就对一大片地区的民众进行隔离。中国既有这种组织力,同时又不伤害正当性。但是在西方做不到,因为这既会伤害它的正当性,它也没有这种高效的组织力。
但这些刚才说的这些都与制度优势或者劣势什么的没有关系,我称之为这是一个“制度特性”或“制度效果”。禁足会不会伤害政体的正当性,这是一个制度特性;无法有效禁足,会影响控制疫情的能力,这是制度效果。但这些都无法直接转换为对制度的优势或劣势的判断。
特性或效果是一个事实判断,优势或劣势是一个价值判断。现在国内的讨论当中经常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同,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
《巴伦周刊》:中国疫情防控较好,复工复产较快,货币政策保留空间较大,人民币也保持强势。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判断变得特别乐观,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施展:整体上我确实看好中国经济,但我也要强调,这跟制度优劣势无关,我做的仅仅是个事实判断,并不关乎任何价值判断。我的看好,指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5到10年内不会遭遇实质性的问题,除非又出现一个我们今天完全意想不到的巨大黑天鹅事件。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内,我不认为中国的实体经济会遭遇会到什么问题。
但随着时间拖长,gdp统计的意涵会改变,仅仅基于数值来说中国的经济前景,意义不大,必须看经济的结构。要看你在忙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你是每天忙着搬砖,还是每天忙着码字?虽然都很忙,但不同的忙活,在社会上的结构性位置、议价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03、平台型企业具有社会公共品的性质
《巴伦周刊》:疫情除了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很大变化,还在企业领域带来了更强的马太效应,比如说全球的互联网巨头和平台型公司都逆势发展,越小的企业可能受损越严重,这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反弹,您能说说对互联网产业反垄断的看法吗?
施展:首先,怎么定义垄断就是个问题。我在《破茧》这本书里面引用了一本书叫做《激进市场》,那里面就谈到垄断。比如你要去买房子,没有哪两个房子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单元门里的房子,不同的楼层,它的采光也不一样。
所以你买下某一个房子,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一样的东西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对这个独一无二的房子就垄断了,只要是垄断就会有租的存在。要是把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追到极端,那么除了大宗商品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均质化的,只要非均质化,就存在垄断,就存在租。《激进市场》里就此衍生出一系列极富想象力的讨论,在这就不展开了,继续咱们的话题。
咱们这话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不用蚂蚁金服,我仍然可以用微信支付。我在社交软件上不用微信,也可以用钉钉,还可以用飞书,可以用whatsup,我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在企业试图基于垄断地位对我进行控制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它,另找一个东西来替代。实际上没有什么产品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它真的构成垄断吗?
刚才这俩例子,从两个比较极端的方向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觉得有垄断的地方,可能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我们觉得有垄断的地方,似乎它也未必真的是垄断。到底什么是垄断?这个问题,学界到现在也没有统一的观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没有统一的观点。所以反垄断究竟效果会怎样,这一点我也是很谨慎的。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也在流传张维迎教授的一篇演讲,里面谈到垄断分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准入制的,不经批准你就不能进来;而市场性垄断,是我干得比你好,但是我没有准入制,你进不来是因为你没我干得好。我为了维持垄断地位,仍然要不断提升我的服务,否则我就被人替代了。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混在一起来看。对于市场性垄断的反垄断效果,我是很谨慎的。
不过,看这问题还有另一个角度。我认为现在监管蚂蚁金服这类的企业,不能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马云说中国根本还没有金融系统,所以何来系统性金融风险?我能明白马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当然有系统,蚂蚁本身就构成一个系统了。哪怕你是个私营企业,只要你的规模足够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从产权上来说你仍然是个私营企业,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你就不再仅仅是私营企业了,你开始成为公共品,也就相应地必须承担起大量的社会责任,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盈利的责任了。
这样的巨头,作为公共平台,就不能完全用商业标准来做评判。可能有人会反对我的这个说法,说这是让商人背上不应有的包袱,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中小商人,我会同意这种批评,但如果讨论的是巨头平台,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更容易说明白这问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书中提出,当时法国和意大利在凡尔赛和约中要向德国压榨极大数额的赔款。为什么呢?除了民族主义激情的冲动外,还有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和意大利都欠了英国和美国大量的战债,而为了能够还得起债,它们就只得从德国那里榨钱。
在这种情况下,英美该怎么做呢?凯恩斯说英美就应该主动放弃这些战债。按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凭什么要人放弃战债呢?关键是战争贷款跟商业贷款完全不是一回事,商业贷款当然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战争贷款是一笔政治贷款,政治贷款意味着,你是否要收回这笔贷款,判断标准是,收款这件事情是否符合你最初发放这笔贷款时的政治目的。
如果收这笔贷款所带来的政治效果,会跟你最初的政治目的正好相反——也就是很可能带来下一场战争的话,那么此时你就应当放弃这笔贷款。但也不能要求英美白白放弃战债,它们应该牵头成立一个超越于各国之上的国际经济组织,以此来克服各国的民族主义激情在全球经济中会带来的巨大问题,而法国、意大利等欠了战债的国家,则应该接受英美在这个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主导地位。
从这个例子再回到刚才我说的监管蚂蚁金服这个问题上。从商业意义上,反垄断是否有正当性?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学界对这个事也没有共识。但是企业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平台之后,成为了社会公共品,就有了巨大的社会责任,对这社会责任就不能用商业标准来判断了。所以从社会责任是否履行到位的意义上来说,对蚂蚁金服进行有效的监管,我是认同的,但这种意义上的监管和反垄断是不同的两回事。而蚂蚁一方面应当接受社会责任意义上的监管,同时因为它在提供新式的公共品,也应当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向蚂蚁释放出来,这才是公平的,也会激励更多企业担当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我在书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但是说得比较简略,很多人可能看的时候一带而过,因为那个概念也是大多人都不熟悉的,就是隐私计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现在正在发展起来。
现在互联网巨头的做法都是搜集用户数据上传到自己的云服务器上,然后在平台上用算法处理,给用户推送相应内容。数据上传经过算法的处理后,基本消费者对企业就是透明的了,隐私都被企业拿走了。
但隐私计算的玩法是,数据不上传,算法下传,算完了的结果再上传。而下传的算法在消费者终端上进行运算的时候,数据是什么,算了多少次,等等内容全都是加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就是说这些隐私仍然在用户自己的手上。同时,隐私算法还能保证消费者仍然可以享有现在互联网的所有便利。
比如在现实生活当中您有个真实身份,在网上您又有一个虚拟的身份叫阿龙,这个虚拟身份实际上就对应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同时也是你的数字钱包。你所有的数据都是以阿龙这个虚拟身份或说账号为载体而生成的,隐私计算可以保证,一方面,人们无法把阿龙对应到您的肉身上,另一方面,阿龙背后又有一个可被验证的真实存在,也就是一个匿名的真人,信用是真实的,各种交易也是可以放心展开的。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巨头可以根据阿龙这个账号的喜好来给他推荐相应的内容,账号的所有者仍然拥有过去的便利,却并不把自己的隐私向平台敞开。而平台去推送这些消息或内容的时候,实际上卖广告的过程就可以展开了,阿龙还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分红。
04、隐私计算、信息茧房与养蛊自噬
《巴伦周刊》:您说的这种前景当然很美好,但是比如说我们在疫情中间看到可能是网络身份和个人身份已经绑定得越来越紧了。
施展:隐私计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政府是没有动力去采用隐私计算的,因为它就掌握不了数据了嘛。但这不是政府想不想采用的事儿,有另外一个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往那个方向转型。
那是什么压力呢?最近一个信息可能你也注意到了,就是google前一段时间宕机了,而且这不是它第一次宕机了,最近这几个月google接连宕机。为什么会宕机呀?因为储存的数据太多了,它的服务器受不了了。连google都受不了了,可以想见别的公司会更快受不了。
随着5g、物联网的到来,连接到网络上的节点数会成数量级地增多,节点间发生各种交互,上传的数据量会是几何级数乃至指数级数地增长,到那会儿所有公司的服务器全都会受不了,没有任何一家云服务商能够受得了那种数据量。到那时,隐私计算就不得不采用办法了,因为它需要传递的信息量要小太多了。
《巴伦周刊》:您的意思是说,企业会因为成本收益的考虑主动放弃把用户的数据占为己有?
施展: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巨头们会放弃把数据上传,选择用算法下传,然后在各家都在这么做的时候,它们又会开始比拼一个新的东西,你在下传的时候我也在下传,同时我可以明确告诉用户,我的下传算法是隐私算法,什么叫隐私算法?你的数据里面的具体内容我全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阿龙,我完全对应不上真人。那么用户肯定都被我吸引走了,因为他们的隐私得到了我的尊重和保护嘛,这种情况下,就没别的企业事了。
而且我肯定不是空口说的,我的算法和代码都可以公开——现在不少企业都在这么做——任何人都可以来查一查,看我是否真的是隐私算法,看我有没有撒谎。那么一旦到了这一步,你会发现用户都被我给吸引走了,你就不得不也采用隐私算法,就会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
《巴伦周刊》:您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判断一直是比较分开的,但在2020年之后,这两者似乎被捆绑得更紧了。您觉得企业真的能实现“去国家化”吗?
施展:这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这些企业现在全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任正非是很反对用民族情结来绑架华为的,在去年舆论中,华为要有点抗美援朝中上甘岭的味道了,任正非马上就在内部说,我们不要用民族情绪来绑架自己,这会伤及我们自身。大的企业家没有谁想被这么绑架,这会让企业陷入莫名其妙的困境当中。
再看美国,google和facebook,同样不想被国家情绪所绑架。现在欧盟出台了一个新规,号称史上最严的数字管理规则。最头疼的肯定不是tiktok,而是facebook,facebook在欧洲的业务的比字节跳动大多了。所以这些巨头都有摆脱国家的约束,中立于国家之外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如何最终能够落实,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个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站在它们的立场上,你会发现,民族主义情绪越高涨越是绑架它们,它们就会产生越强的中立化需求。一个企业被民族主义绑架,结果就是它无法成为全球企业,只能作为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性企业。你要想成为全球性企业,必须得别的国家愿意让你进去,而别的国家愿意让你进去,前提是你不能携带一系列的民族主义情绪进来,所以越是全球化的企业,越有让自己中立性的需求。
只不过这个需求最终怎么实现,这些企业家们未必想得清楚,需要有更多人一块来想这个问题。我在《破茧》一书的整个第三部分都是在谈这个问题,所有那些讨论实际上都只是尝试打开脑洞,尝试用我这本书作为靶子,把问题提出来,吸引更多人一块来讨论这个问题。
《巴伦周刊》:这本书书名是《破茧》,但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似乎还是没有回答信息茧房到底应该怎么破解?
施展:实际上我在书里面已经写到了,但出版后我在反思时,意识到我没有写清楚。我提到了,信息茧房可能需要某些公共事件才能被打破,借助一个公共事件来把所有人的茧房都给冲开,把墙壁冲碎,但这只是破坏性的,还不是建设性的。
建设性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的信息茧房,它的一个很重要成因在于推荐算法,推荐算法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商业模式,只要是好的商业模式,用政策控制是控制不住的,但是信息茧房也会给使用它的公司带来一系列反噬效应。
比如像字节跳动,它是推荐算法应用得非常到位的一个企业。但是今天它也遭遇到反噬了,因为推荐算法强化了信息茧房,而在信息茧房下,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这就像养蛊一样,这些被信息茧房培育出来的民族主义,最终反噬了字节跳动,让字节在面对美国巨大压力的时候,它的言论空间、决策空间反倒被大幅压缩了,它被民族主义所绑架了。这些绑架它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一部分就是它的信息茧房给喂养出来的。
在未来,企业逐渐都会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反噬效应,推荐算法本身很可能会演化出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要保证不会把人给困在信息茧房里面,这不是因为这些企业善良,而是因为这样才符合它们的利益。如果推荐算法在今天会让这些企业养蛊自噬,那么在这种恐惧下,一种新的商业伦理就可能会浮现出来。未来突破信息茧房突破的前景就在此。
《巴伦周刊》:谢谢您。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