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笔者这一代“七零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这是流行音乐和电视娱乐文化主宰的时代,对于西方,一般都有积极的憧憬和向往。在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中西对比极为敏感的父母,更是容易把“出国”的希望寄望在这一代人的身上。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过多,经济远比西方落后所造成的焦虑感到处蔓延,知识界甚至一度声称,中国可能被“开除(地球)球籍”。
当笔者在1991年进入大学时,改革开放处于暂时的低潮,但是对外界的兴趣和向往并没有消退。在笔者所在的学校和专业,每个学期都有来自英语国家的外籍教师,全职对我们进行分项的英语训练,其中包括日常可以自然接触和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读物。
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教师为我们带来更为活泼的教学方式,比如在教室里环坐成一圈讨论,轮流的英语口头时事报告(记得有一次我的报告内容是当时轰动一时,一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挨鞭刑的新闻事件)、英语辩论等。有的教师也和学生建立了不错的情谊。
我们知道有的美国教师在美国过得并不怎么好,要靠家人资助,有的喜欢在不同的亚洲国家教英语谋生,同时体验不同文化,有的和学校也发生过关于待遇方面的纠葛,有的特别爱吃烤鸭,有的亚裔教师特别注重亚裔的自主性。
但是,由于课程设置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学校的要求,导致“外教”的主要功能还是局限于语言训练,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深入教授西方的制度、历史、宗教、文化。对英美社会的学习,不过局限于“概况”式的简介,虽然是英文原版教材,但介绍的内容几乎是旅游指南式的浮光掠影。
笔者在今天反思时认为,如果在我们的这种已经显得很受西方语言和文化影响的校园里,仍然缺少对西方的深度认识,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更是严重受限。
就“外教”来说,除了把学生引入好莱坞电影(如当时流行的home alone《小鬼当家》)这样的大众文化以外,也没有任何动力,和相应的课程及阅读材料,把学生引入对美国历史、社会和对政治的全方位认识。有的外教也确实只是敷衍应付,因为向已经初步掌握英文的中国学生教授自己的母语,实在说不上多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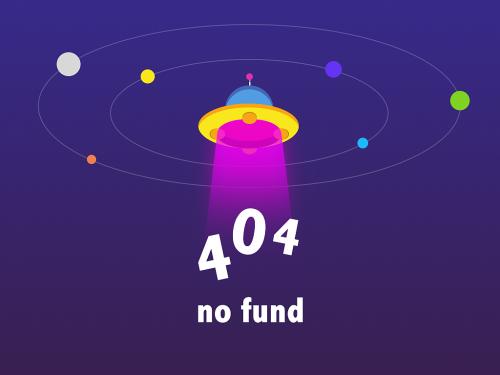
即使很多年以后,“外教”在中国的各类培训机构中已经随处可见,其传授内容也仍然超不出“教英语”这个基本范畴,而“外教”也乐得维持美国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那种“好莱坞”式的半虚幻形象。
一名外教曾经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在几点之前交作业,过了时间就拒收,而我们从来没想过去讨价还价,全都严格遵守她的规定。但在美国任教后,笔者才发现,找出种种借口讨价还价,要求延期,是美国大学生的常态。
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自认为已经很了解美国的人的信息来源,常常是中国国内的涉美新闻、家人和亲戚中定居美国或留学的成员,而不是严格的阅读和思考训练及深度剖析。
认识其他区域的知识基础
然而,美国在二战以后,就已经发展起来一套以美国为中心和出发点,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体制。在全球化时代,又进一步以在下一代中培养具有领袖意识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为目标,以“多元化”(diversity)为旗号,大力吸纳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学者,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让来自某个国家的人讲自己的国家,并最终服务于美国人认识和研究他国的庞大知识基础工程。
在这个计划中,语言教学只是一个组成部分。在阿拉伯语的教学中,来自中东的学者也会开设关于中东政治和宗教的课程。以涉及中国的内容为例,在中文教学以及更进一步的文学和电影分析以外,笔者接触和认识的华裔学者,分布在美国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哲学/宗教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及东亚研究系科。他们把自己在中美两地的严谨学术训练,以及某些实地的人生体悟结合起来,使美国大学生可以通过课堂的详细解剖,获得极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洞见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华裔学者在这种有关中国的教学互动中的特殊作用,是缺乏在中国长期生活经历的美国普通中国研究学者所不具备的。同时,华裔学者的自我要求也很严格。笔者认识的一位华裔历史学教授,曾反思如何排除个人经历和情感对历史教学的干扰;另一位同行也提示华裔学者不要在教学中过度“自我代入”。
当然,笔者认为,“自我”既然存在,绝对不“自我代入”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学者在讲授中国的时候,会自然地说“他们”(they)如何如何;而在中国长大,以中文为母语的华裔学者,会很自然地在课堂上用“they”来描述中国人吗?
此外,由于在美华裔学者除了少数供职于顶尖研究型大学外,大多数就职于普通的公立大学分校校园和小型文理学院,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并不会成为研究中国的学者,而是成为具备对中国有较深入了解,并通过有深度的阅读和分析写作训练,而对一些特定问题有相当认识的普通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对华认知,必定比中国国内只注重英语语言学习的群体的对美认识更立体、更全面、更具有理论和实证基础。
笔者提出的“知识逆差”,就是指这种不对等现象。在中国出生的海外华裔学者,由于职业的要求,在大学课堂上向未来的美国中产阶级有系统、有学科背景和框架地传输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分析和研究角度,并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地阅读、写作和初步研究。
这一过程中的知识输出,其数量和质量以及参与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外教”在中国所进行的简单、随意、浅层的传播,而且后者最多接受过在海外教授英语(tesol)或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的训练,既没有深度的社会科学背景,更没有被吸纳进中国的大学学科和评估体制,其间还混杂了不少不学无术的“洋混混”甚至不法分子。由此,双方的传播质量存在严重的不对等。
基于中美两国国家体制,移民政策的区别,中国注定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自己的大学里系统讲授外国,并接受同等的教学科研评价。
这样的现状的结果,就是在相似的阶层中,美国人对中国有较深度了解的人,会超过中国人对美国真正有了解的人;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制度和文化出现误判的概率,也极可能会大于美国对中国误判的概率。因为真正有效的判断,必定建立在具有学理基础和深度分析的研读和思考之上,这和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对美国的简单了解,并非一回事。
由于中国国内缺少“外国人讲外国”的制度安排和学术环境,或许也缺少培养“全球公民”的宏大计划,而是出现中国网红吹嘘中国,美国(西方)网红也跟风吹嘘中国的社会怪象,难免导致一流大学的学生,对世界的认知也受到局限,变得网络化、快餐化、流俗化。
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指出,清华学生“居高临下”看世界,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以令人信服的客观、严谨,以及平衡的态度,把真实的外部世界告诉中国学生的一个机制。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笔者这一代“七零后”,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这是流行音乐和电视娱乐文化主宰的时代,对于西方,一般都有积极的憧憬和向往。在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中西对比极为敏感的父母,更是容易把“出国”的希望寄望在这一代人的身上。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过多,经济远比西方落后所造成的焦虑感到处蔓延,知识界甚至一度声称,中国可能被“开除(地球)球籍”。
当笔者在1991年进入大学时,改革开放处于暂时的低潮,但是对外界的兴趣和向往并没有消退。在笔者所在的学校和专业,每个学期都有来自英语国家的外籍教师,全职对我们进行分项的英语训练,其中包括日常可以自然接触和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读物。
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教师为我们带来更为活泼的教学方式,比如在教室里环坐成一圈讨论,轮流的英语口头时事报告(记得有一次我的报告内容是当时轰动一时,一名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挨鞭刑的新闻事件)、英语辩论等。有的教师也和学生建立了不错的情谊。
我们知道有的美国教师在美国过得并不怎么好,要靠家人资助,有的喜欢在不同的亚洲国家教英语谋生,同时体验不同文化,有的和学校也发生过关于待遇方面的纠葛,有的特别爱吃烤鸭,有的亚裔教师特别注重亚裔的自主性。
但是,由于课程设置的原因,也可能由于学校的要求,导致“外教”的主要功能还是局限于语言训练,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深入教授西方的制度、历史、宗教、文化。对英美社会的学习,不过局限于“概况”式的简介,虽然是英文原版教材,但介绍的内容几乎是旅游指南式的浮光掠影。
笔者在今天反思时认为,如果在我们的这种已经显得很受西方语言和文化影响的校园里,仍然缺少对西方的深度认识,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更是严重受限。
就“外教”来说,除了把学生引入好莱坞电影(如当时流行的home alone《小鬼当家》)这样的大众文化以外,也没有任何动力,和相应的课程及阅读材料,把学生引入对美国历史、社会和对政治的全方位认识。有的外教也确实只是敷衍应付,因为向已经初步掌握英文的中国学生教授自己的母语,实在说不上多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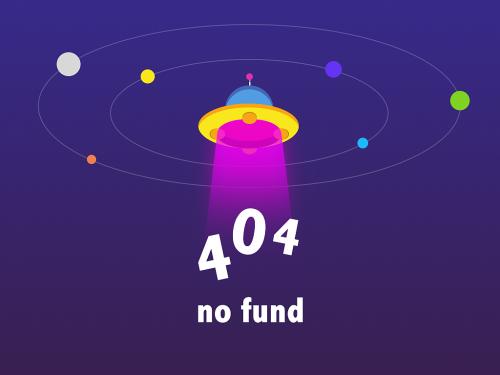
即使很多年以后,“外教”在中国的各类培训机构中已经随处可见,其传授内容也仍然超不出“教英语”这个基本范畴,而“外教”也乐得维持美国在外国人心目中的那种“好莱坞”式的半虚幻形象。
一名外教曾经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在几点之前交作业,过了时间就拒收,而我们从来没想过去讨价还价,全都严格遵守她的规定。但在美国任教后,笔者才发现,找出种种借口讨价还价,要求延期,是美国大学生的常态。
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自认为已经很了解美国的人的信息来源,常常是中国国内的涉美新闻、家人和亲戚中定居美国或留学的成员,而不是严格的阅读和思考训练及深度剖析。
认识其他区域的知识基础
然而,美国在二战以后,就已经发展起来一套以美国为中心和出发点,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综合性、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体制。在全球化时代,又进一步以在下一代中培养具有领袖意识的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为目标,以“多元化”(diversity)为旗号,大力吸纳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学者,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让来自某个国家的人讲自己的国家,并最终服务于美国人认识和研究他国的庞大知识基础工程。
在这个计划中,语言教学只是一个组成部分。在阿拉伯语的教学中,来自中东的学者也会开设关于中东政治和宗教的课程。以涉及中国的内容为例,在中文教学以及更进一步的文学和电影分析以外,笔者接触和认识的华裔学者,分布在美国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哲学/宗教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及东亚研究系科。他们把自己在中美两地的严谨学术训练,以及某些实地的人生体悟结合起来,使美国大学生可以通过课堂的详细解剖,获得极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洞见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华裔学者在这种有关中国的教学互动中的特殊作用,是缺乏在中国长期生活经历的美国普通中国研究学者所不具备的。同时,华裔学者的自我要求也很严格。笔者认识的一位华裔历史学教授,曾反思如何排除个人经历和情感对历史教学的干扰;另一位同行也提示华裔学者不要在教学中过度“自我代入”。
当然,笔者认为,“自我”既然存在,绝对不“自我代入”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学者在讲授中国的时候,会自然地说“他们”(they)如何如何;而在中国长大,以中文为母语的华裔学者,会很自然地在课堂上用“they”来描述中国人吗?
此外,由于在美华裔学者除了少数供职于顶尖研究型大学外,大多数就职于普通的公立大学分校校园和小型文理学院,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并不会成为研究中国的学者,而是成为具备对中国有较深入了解,并通过有深度的阅读和分析写作训练,而对一些特定问题有相当认识的普通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对华认知,必定比中国国内只注重英语语言学习的群体的对美认识更立体、更全面、更具有理论和实证基础。
笔者提出的“知识逆差”,就是指这种不对等现象。在中国出生的海外华裔学者,由于职业的要求,在大学课堂上向未来的美国中产阶级有系统、有学科背景和框架地传输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分析和研究角度,并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地阅读、写作和初步研究。
这一过程中的知识输出,其数量和质量以及参与人数,都远远超过美国“外教”在中国所进行的简单、随意、浅层的传播,而且后者最多接受过在海外教授英语(tesol)或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的训练,既没有深度的社会科学背景,更没有被吸纳进中国的大学学科和评估体制,其间还混杂了不少不学无术的“洋混混”甚至不法分子。由此,双方的传播质量存在严重的不对等。
基于中美两国国家体制,移民政策的区别,中国注定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自己的大学里系统讲授外国,并接受同等的教学科研评价。
这样的现状的结果,就是在相似的阶层中,美国人对中国有较深度了解的人,会超过中国人对美国真正有了解的人;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制度和文化出现误判的概率,也极可能会大于美国对中国误判的概率。因为真正有效的判断,必定建立在具有学理基础和深度分析的研读和思考之上,这和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对美国的简单了解,并非一回事。
由于中国国内缺少“外国人讲外国”的制度安排和学术环境,或许也缺少培养“全球公民”的宏大计划,而是出现中国网红吹嘘中国,美国(西方)网红也跟风吹嘘中国的社会怪象,难免导致一流大学的学生,对世界的认知也受到局限,变得网络化、快餐化、流俗化。
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指出,清华学生“居高临下”看世界,在笔者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以令人信服的客观、严谨,以及平衡的态度,把真实的外部世界告诉中国学生的一个机制。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