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按历史惯例,一个战功赫赫的强力将领当上了国家元首,多半演化成军事强人的长期独裁统治,将国家治理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经济文化上封闭保守,整个国家事业陷于停滞。这在那个年代更是非常常见的。
但幸运的是,凯末尔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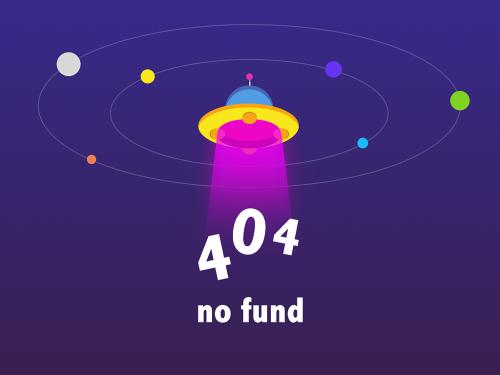
凯末尔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少年军校(初中)-青年军校(高中)-陆军军事学院(大学)一路度过的,尽管是全封闭严格管理的军事学校,从西方传来的现代革新思想却在私底下广泛传播。就连那些军校教官们,也对奥斯曼王朝落后无望的统治非常不满,并经常把这种情绪和思想流露和传染给学生。
学院中严禁阅读报纸,除了教科书外不准看其他书籍。但“违禁书籍”仍然在学员中偷偷流传,凯末尔的床铺底下也藏着这样的书:
加里波第的传记、烧炭党人的小册子、波兰革命者的诗集,以及伟大的启蒙主义一代作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等等。
军校不只为帝国培养未来的军事指挥官,还成了培养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情感的中心。外敌入侵与内部分裂,国家一溃千里的局势令任何有爱国心的青年军官都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改换政体,结束腐败无能的君主专制。
la partrie、liberte、egalite、fraternite——祖国、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时推翻王政的口号深植于青年军官们的内心。
就在凯末尔军校毕业前夕,他在军校中的秘密阅读活动和其他不安分守己的行为早已被学生密探告发,他和几名同学被逮捕入狱。
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凯末尔上尉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然后发配到远在叙利亚的部队服役。但即使在帝国边疆的部队里,青年军官们的秘密革命组织也在活跃的活动。
这一切在凯末尔成长的年代毫不奇怪,奥斯曼帝国那些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对苏丹的统治非常不满,君主专制统治、严格的新闻钳制和出版审查并不能阻挡民主、自由这类“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的蔓延。
讽刺的是,帝国把这些人当作未来的军事和行政精英来培养,给予他们最先进、最现代化的教育。而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教师经常讨论的却是如何对老朽垂死的帝国传统体制进行彻底的革命式改造。
一个冒着风险读着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三权分立、人民主权启蒙思想长大的现代军人,他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崇尚武力愚昧无知的赳赳武夫了。
初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幸运,不仅在于有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将领开国定疆,还在于拥有了一个既深具现代思想,又极富执行力的的改革者,更幸运的是——这两位是同一个人,并且他就是声望卓著的国家元首。
而当年那位不安分的军校学员穆斯塔法,也终于从尉官、校官、将官一路走来,用自己亲手缔造的胜利,开启了自己可以施展宏图的时代。
总统凯末尔脱去了元帅制服,穿上了西式礼服,戴上了礼帽,土耳其共和国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了。
改革肇始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首先是1924年确立的世俗主义宪法,然后是政教分离,建立欧式的法律与司法体系。接下来,行政系统也被彻底世俗化和现代化了,尤其是教育体制的大改革。
改革的核心价值观是土耳其社会必须在文化上与政治上西化,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将被称为凯末尔主义。
因为在凯末尔看来,国家正确的道路必须是世俗化、西方化、现代化,与主流世界文明接轨。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凯末尔说,为了生存下去,上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核心在宗教上,因为他坚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科学民主的理念互相矛盾,两者无法共存。
1924年3月3日,凯末尔废除了苟延残喘的哈里发制度,将前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并且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制,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法),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极端宗教集团的教产被没收,把伊斯兰教彻底从国家权力体系中清除了出去。
同时,制订和采用依据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刑法典为摹本的现代化新法律体系,宗教教育系统为国民教育系统所取代,建立宗教事务管理局,从而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障碍。到1928年,宪法上原有的“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一句亦被移除,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土耳其在政治上完全成为世俗国家。
除了大力确立政教分离体制,凯末尔还希望能够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土耳其落后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进行全面再造。他对土耳其的每件事物,从衣帽头饰到口头语言,都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有必要的地方统统革新。
在凯末尔看来,如果要保证世俗主义永存,由宗教标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就必须消失,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公众在文化上接受以后更进一步的改革。随之而来的便是1925年的“服装法令”。
法令禁止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宗教徽记,特别是禁止所有男子戴非斯帽(土耳其无檐毡帽,便于祈祷时能不脱帽以头触地),它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残留物,因此是封建保守的象征)。尽管几个世纪来都被视为土耳其人的象征,凡戴土耳其帽者仍将依律治罪。
到1934年,另一项新的限制服装的法律获得通过。法令禁止任何基于宗教的服饰,这就等于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政府同时积极推动西式服装的普及,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凯末尔带头脱下军服,换上西服,以为国民表率。
同时,适应新民法的需要,大国民议会还下令所有土耳其公民都要有自己的姓氏(此前奥斯曼帝国上至苏丹下至乞丐,都是有名无姓),同时废除“帕夏”、“贝伊”、“加齐”、“阿凡提”等所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官衔、爵位和称呼,,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
比取缔宗教服饰更重大的变化在于语言改革。1928年由凯末尔亲自主持的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设计了基于国际通行拉丁字母的新文字体系,用拉丁字母来标注突厥发音,取代了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大国民议会随即立法,从第二年元旦开始,就不再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
因为阿拉伯语字母只有少数伊斯兰学者才能读懂,废除它断绝了与奥斯曼伊斯兰文献的联系,表现了共和国的世俗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拉丁字母更使得学习读写更容易,最终提升识字率。
凯末尔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
身为总统的凯末尔亲自前往全国各地,在乡村的广场、学校的教室、市镇的咖啡馆里亲自教人民认识全新的字母表。在凯末尔的带动下,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纷纷效仿,新字母普及活动遍及全国,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教室。为了表彰凯末尔在文字改革中的巨大成就,大国民议会授予他“国民学校总教师”的称号。
在宗教和文字改革的基础上,教育和技术改革也全面铺开。废除了宗教学校,国民教育实现统一的现代体制。此外还有通过新的著作权法,建立公共教育以及科学出版的出版社,并促进私营出版业界的发展,以此来推动教育和科学进步。
在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1924年采用了新的周末法案,周末由原来的伊斯兰圣日星期五调至基督教体制的星期日),1925年采用国际时间与日历系统(公历,也就是基督教的格里高利历),废除传统的伊斯兰历法;1933年规范度量衡,遵从国际单位制,从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西方社会而非中东接轨。
凯末尔尊重伊斯兰教,自己也会做礼拜,但作为政治家,他要从社会舞台上移除伊斯兰学者阶级的存在,或者至少要遏制他们对政治的重大影响。凯末尔主义将那些“不科学的人”、“不具实证主义精神的人”、“在迷信的界限内运作的人”定义为“不文明的人”,将其称为“gerici”(反动者)。
凯末尔还试图去除草药、药水和精神、宗教疗法的迷信成分(这些都是伊斯兰传统医术的一部分),驳斥那些用草药、药水和药膏来行医的人,并且处罚那些自认为对健康和医学有研究的人,用掌握现代医学的专业医生去取代旧有的医疗体系。
作为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凯末尔说到,“我断然拒绝相信,在科学、知识、文明都全方位闪亮登场的今天,在文明的土耳其社会里,还会存在这样的人,仍然在这个或那个教长的指导下,愚蠢地去寻找他们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更加超越时代的是,凯末尔推动了一系列提高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改革。包括在法律中明文强制不准妇女戴面纱、废除一夫多妻、废除休妻制确立离婚制度。野蛮落后的“荣誉谋杀”(家族中男性可以杀死失贞的女儿或妹妹)更是宣布为非法。
同时,保障妇女在教育、就业、参政及财产继承的平等权利,鼓励妇女们积极参加国家生活。
在1934年修改的宪法中,妇女21岁拥有选举权,30岁则拥有被选举权,这项举措甚至比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要更早,更何况一个在穆斯林国家,用惊世骇俗一词毫不为过。
在1934年底的大选后,1935年初,18名女性国会议员加入土耳其国会,而当时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女性连投票的权利都还没有。凯末尔的女性权利改革,“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突破,也是西方世界的突破”。
凯末尔将这一切社会改革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意志蓝图推动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
土耳其现代化的另一项艰巨任务是振兴经济。奥斯曼帝国长期经济落后,毫无国家工业可言。自1912年巴尔干战争起,本土又不间断地遭受了10年的战争摧残,到处都是国敝民穷、哀鸿遍野。虽然《洛桑和约》免除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战争赔款,但仍然必须偿还奥斯曼帝国留下的众多公债和外债。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凯末尔推行国家化、现代化和工业化政策,建立众多国有工厂,包括机器制造厂和纺织业工厂,建立示范农场,发展交通网络。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下,仍花费巨资从西方资本家手里赎买铁路、矿山、自来水、电车等公用事业。政府大力推动进口替代战略,并且成立国有银行来振兴产业。
为了获得资金,土耳其不得不仿照苏联的做法,冻结甚至降低居民消费水平,实行高税收和高关税政策,以及采用工农业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来完成原始积累。
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土耳其也仿效苏联制订五年计划。而与面临强大外部敌人的苏联不同,国际压力小得多的土耳其可以以优先发展轻工业为主。
此外,凯末尔相当的精力还花在了新共和国的新首都安卡拉的建设上,当他于1920年在此建立他的临时政府时,这里只是一个布满灰尘的小城,仅有3万人口。但当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它成为土耳其的新首都,并着手发展、建设城市。
在向一些欧洲城市规划者咨询后,安卡拉被建成拥有宽阔林荫道、包括人工湖在内的森林公园、广阔居民区的城市。它在土耳其地理中心的位置,使得其不管是从战略安全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比在国家版图里已经偏居黑海海峡一隅的君士坦丁堡,更加适合成为新共和国的首都。
这样,外国的海军再也不能威胁到这个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中心的首都;而它的建设又能引领和带动贫瘠的、尘土飞扬的广大高原地区,平衡全国的发展。
从1919年到1927年,阿塔图尔克从未涉足繁华的君士坦丁堡,而是一直致力于将安卡拉建设为真正的全国中心。而君士坦丁堡也在1930年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俗称已经被用了几个世纪。
在外交方面,凯末尔提出了“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口号,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自从独立战争伊始,土耳其就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法国和意大利也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与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1926年,土耳其和英国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土耳其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视其为本民族一部分)聚居的摩苏尔地区归属问题达成协议;摩苏尔划归伊拉克,土耳其每年获得摩苏尔油田10%的收入。此后,长期冷淡的土英关系也逐渐实现正常化。1932年,土耳其在英国支持下加入国际联盟。
在巴尔干方面,凯末尔恪守公约,放弃了对马其顿、西色雷斯和鲁米利等一切已丢失领土的要求。甚至不惜在刚刚停战建国的1924年,就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将生活在两国的对方民族人口进行大对换。
在两国政府的安排下,生活在希腊北部和和爱琴海岛屿上的土耳其人全部撤回到土耳其,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全部撤回到希腊。
总共有200万人离开了他们原先的家乡,被安置在母国同样是人去楼空的村子里。人口大交换的目的是彻底消除种族冲突的隐患,同时打消了邻国的顾虑。
凯末尔还取缔了原先执政者鼓吹的“泛突厥主义”,只注目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再关注“东突厥”(即哈萨克与中亚的突厥)。凯末尔对此不感兴趣,只着眼于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现存及历史的文化中的土耳其人。
在20年代,土耳其先后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订了友好条约,并在30年代同希腊建立了友好关系。1932年,希腊首相维尼齐洛斯甚至提名凯末尔为193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选人。
到1938年,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土耳其已经建成了基本的工业体系,工业年增长率达10%,同苏联、德国、日本一道被列为当时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凯末尔充满传奇色彩的不断奋斗和努力下,土耳其不但从被西方列强瓜分宰割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半封建半奴隶制帝国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从一个伊斯兰神权君主制国家变成了议会立宪制共和国;从官僚封建主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走上经济发展正轨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
在1930年代,凯末尔国家主义政策所创造的奇迹不仅为土耳其人所敬佩景仰,而且在波斯、阿富汗、中国、印度等仍然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之苦的东方民族和国家中引起重视,“土耳其模式”成了东方国家救亡图存,摆脱列强压迫的希望之一。
按历史惯例,一个战功赫赫的强力将领当上了国家元首,多半演化成军事强人的长期独裁统治,将国家治理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经济文化上封闭保守,整个国家事业陷于停滞。这在那个年代更是非常常见的。
但幸运的是,凯末尔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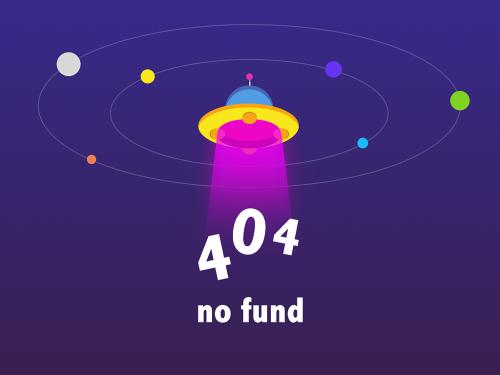
凯末尔
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少年军校(初中)-青年军校(高中)-陆军军事学院(大学)一路度过的,尽管是全封闭严格管理的军事学校,从西方传来的现代革新思想却在私底下广泛传播。就连那些军校教官们,也对奥斯曼王朝落后无望的统治非常不满,并经常把这种情绪和思想流露和传染给学生。
学院中严禁阅读报纸,除了教科书外不准看其他书籍。但“违禁书籍”仍然在学员中偷偷流传,凯末尔的床铺底下也藏着这样的书:
加里波第的传记、烧炭党人的小册子、波兰革命者的诗集,以及伟大的启蒙主义一代作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等等。
军校不只为帝国培养未来的军事指挥官,还成了培养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情感的中心。外敌入侵与内部分裂,国家一溃千里的局势令任何有爱国心的青年军官都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改换政体,结束腐败无能的君主专制。
la partrie、liberte、egalite、fraternite——祖国、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时推翻王政的口号深植于青年军官们的内心。
就在凯末尔军校毕业前夕,他在军校中的秘密阅读活动和其他不安分守己的行为早已被学生密探告发,他和几名同学被逮捕入狱。
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凯末尔上尉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然后发配到远在叙利亚的部队服役。但即使在帝国边疆的部队里,青年军官们的秘密革命组织也在活跃的活动。
这一切在凯末尔成长的年代毫不奇怪,奥斯曼帝国那些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对苏丹的统治非常不满,君主专制统治、严格的新闻钳制和出版审查并不能阻挡民主、自由这类“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的蔓延。
讽刺的是,帝国把这些人当作未来的军事和行政精英来培养,给予他们最先进、最现代化的教育。而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教师经常讨论的却是如何对老朽垂死的帝国传统体制进行彻底的革命式改造。
一个冒着风险读着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三权分立、人民主权启蒙思想长大的现代军人,他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只崇尚武力愚昧无知的赳赳武夫了。
初生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幸运,不仅在于有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天才将领开国定疆,还在于拥有了一个既深具现代思想,又极富执行力的的改革者,更幸运的是——这两位是同一个人,并且他就是声望卓著的国家元首。
而当年那位不安分的军校学员穆斯塔法,也终于从尉官、校官、将官一路走来,用自己亲手缔造的胜利,开启了自己可以施展宏图的时代。
总统凯末尔脱去了元帅制服,穿上了西式礼服,戴上了礼帽,土耳其共和国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开始了。
改革肇始于国家机器的现代化,首先是1924年确立的世俗主义宪法,然后是政教分离,建立欧式的法律与司法体系。接下来,行政系统也被彻底世俗化和现代化了,尤其是教育体制的大改革。
改革的核心价值观是土耳其社会必须在文化上与政治上西化,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将被称为凯末尔主义。
因为在凯末尔看来,国家正确的道路必须是世俗化、西方化、现代化,与主流世界文明接轨。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凯末尔说,为了生存下去,上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核心在宗教上,因为他坚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科学民主的理念互相矛盾,两者无法共存。
1924年3月3日,凯末尔废除了苟延残喘的哈里发制度,将前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并且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制,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即伊斯兰法),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极端宗教集团的教产被没收,把伊斯兰教彻底从国家权力体系中清除了出去。
同时,制订和采用依据瑞士民法典和意大利刑法典为摹本的现代化新法律体系,宗教教育系统为国民教育系统所取代,建立宗教事务管理局,从而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障碍。到1928年,宪法上原有的“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一句亦被移除,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土耳其在政治上完全成为世俗国家。
除了大力确立政教分离体制,凯末尔还希望能够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土耳其落后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进行全面再造。他对土耳其的每件事物,从衣帽头饰到口头语言,都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有必要的地方统统革新。
在凯末尔看来,如果要保证世俗主义永存,由宗教标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就必须消失,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公众在文化上接受以后更进一步的改革。随之而来的便是1925年的“服装法令”。
法令禁止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宗教徽记,特别是禁止所有男子戴非斯帽(土耳其无檐毡帽,便于祈祷时能不脱帽以头触地),它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残留物,因此是封建保守的象征)。尽管几个世纪来都被视为土耳其人的象征,凡戴土耳其帽者仍将依律治罪。
到1934年,另一项新的限制服装的法律获得通过。法令禁止任何基于宗教的服饰,这就等于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政府同时积极推动西式服装的普及,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凯末尔带头脱下军服,换上西服,以为国民表率。
同时,适应新民法的需要,大国民议会还下令所有土耳其公民都要有自己的姓氏(此前奥斯曼帝国上至苏丹下至乞丐,都是有名无姓),同时废除“帕夏”、“贝伊”、“加齐”、“阿凡提”等所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官衔、爵位和称呼,,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
比取缔宗教服饰更重大的变化在于语言改革。1928年由凯末尔亲自主持的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设计了基于国际通行拉丁字母的新文字体系,用拉丁字母来标注突厥发音,取代了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大国民议会随即立法,从第二年元旦开始,就不再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
因为阿拉伯语字母只有少数伊斯兰学者才能读懂,废除它断绝了与奥斯曼伊斯兰文献的联系,表现了共和国的世俗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拉丁字母更使得学习读写更容易,最终提升识字率。
凯末尔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
身为总统的凯末尔亲自前往全国各地,在乡村的广场、学校的教室、市镇的咖啡馆里亲自教人民认识全新的字母表。在凯末尔的带动下,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也纷纷效仿,新字母普及活动遍及全国,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教室。为了表彰凯末尔在文字改革中的巨大成就,大国民议会授予他“国民学校总教师”的称号。
在宗教和文字改革的基础上,教育和技术改革也全面铺开。废除了宗教学校,国民教育实现统一的现代体制。此外还有通过新的著作权法,建立公共教育以及科学出版的出版社,并促进私营出版业界的发展,以此来推动教育和科学进步。
在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1924年采用了新的周末法案,周末由原来的伊斯兰圣日星期五调至基督教体制的星期日),1925年采用国际时间与日历系统(公历,也就是基督教的格里高利历),废除传统的伊斯兰历法;1933年规范度量衡,遵从国际单位制,从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西方社会而非中东接轨。
凯末尔尊重伊斯兰教,自己也会做礼拜,但作为政治家,他要从社会舞台上移除伊斯兰学者阶级的存在,或者至少要遏制他们对政治的重大影响。凯末尔主义将那些“不科学的人”、“不具实证主义精神的人”、“在迷信的界限内运作的人”定义为“不文明的人”,将其称为“gerici”(反动者)。
凯末尔还试图去除草药、药水和精神、宗教疗法的迷信成分(这些都是伊斯兰传统医术的一部分),驳斥那些用草药、药水和药膏来行医的人,并且处罚那些自认为对健康和医学有研究的人,用掌握现代医学的专业医生去取代旧有的医疗体系。
作为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凯末尔说到,“我断然拒绝相信,在科学、知识、文明都全方位闪亮登场的今天,在文明的土耳其社会里,还会存在这样的人,仍然在这个或那个教长的指导下,愚蠢地去寻找他们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更加超越时代的是,凯末尔推动了一系列提高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改革。包括在法律中明文强制不准妇女戴面纱、废除一夫多妻、废除休妻制确立离婚制度。野蛮落后的“荣誉谋杀”(家族中男性可以杀死失贞的女儿或妹妹)更是宣布为非法。
同时,保障妇女在教育、就业、参政及财产继承的平等权利,鼓励妇女们积极参加国家生活。
在1934年修改的宪法中,妇女21岁拥有选举权,30岁则拥有被选举权,这项举措甚至比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要更早,更何况一个在穆斯林国家,用惊世骇俗一词毫不为过。
在1934年底的大选后,1935年初,18名女性国会议员加入土耳其国会,而当时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女性连投票的权利都还没有。凯末尔的女性权利改革,“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突破,也是西方世界的突破”。
凯末尔将这一切社会改革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意志蓝图推动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
土耳其现代化的另一项艰巨任务是振兴经济。奥斯曼帝国长期经济落后,毫无国家工业可言。自1912年巴尔干战争起,本土又不间断地遭受了10年的战争摧残,到处都是国敝民穷、哀鸿遍野。虽然《洛桑和约》免除了土耳其共和国的战争赔款,但仍然必须偿还奥斯曼帝国留下的众多公债和外债。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凯末尔推行国家化、现代化和工业化政策,建立众多国有工厂,包括机器制造厂和纺织业工厂,建立示范农场,发展交通网络。在巨额贸易逆差的情况下,仍花费巨资从西方资本家手里赎买铁路、矿山、自来水、电车等公用事业。政府大力推动进口替代战略,并且成立国有银行来振兴产业。
为了获得资金,土耳其不得不仿照苏联的做法,冻结甚至降低居民消费水平,实行高税收和高关税政策,以及采用工农业剪刀差(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来完成原始积累。
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土耳其也仿效苏联制订五年计划。而与面临强大外部敌人的苏联不同,国际压力小得多的土耳其可以以优先发展轻工业为主。
此外,凯末尔相当的精力还花在了新共和国的新首都安卡拉的建设上,当他于1920年在此建立他的临时政府时,这里只是一个布满灰尘的小城,仅有3万人口。但当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它成为土耳其的新首都,并着手发展、建设城市。
在向一些欧洲城市规划者咨询后,安卡拉被建成拥有宽阔林荫道、包括人工湖在内的森林公园、广阔居民区的城市。它在土耳其地理中心的位置,使得其不管是从战略安全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比在国家版图里已经偏居黑海海峡一隅的君士坦丁堡,更加适合成为新共和国的首都。
这样,外国的海军再也不能威胁到这个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中心的首都;而它的建设又能引领和带动贫瘠的、尘土飞扬的广大高原地区,平衡全国的发展。
从1919年到1927年,阿塔图尔克从未涉足繁华的君士坦丁堡,而是一直致力于将安卡拉建设为真正的全国中心。而君士坦丁堡也在1930年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俗称已经被用了几个世纪。
在外交方面,凯末尔提出了“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口号,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自从独立战争伊始,土耳其就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法国和意大利也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与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1926年,土耳其和英国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土耳其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视其为本民族一部分)聚居的摩苏尔地区归属问题达成协议;摩苏尔划归伊拉克,土耳其每年获得摩苏尔油田10%的收入。此后,长期冷淡的土英关系也逐渐实现正常化。1932年,土耳其在英国支持下加入国际联盟。
在巴尔干方面,凯末尔恪守公约,放弃了对马其顿、西色雷斯和鲁米利等一切已丢失领土的要求。甚至不惜在刚刚停战建国的1924年,就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将生活在两国的对方民族人口进行大对换。
在两国政府的安排下,生活在希腊北部和和爱琴海岛屿上的土耳其人全部撤回到土耳其,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全部撤回到希腊。
总共有200万人离开了他们原先的家乡,被安置在母国同样是人去楼空的村子里。人口大交换的目的是彻底消除种族冲突的隐患,同时打消了邻国的顾虑。
凯末尔还取缔了原先执政者鼓吹的“泛突厥主义”,只注目于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再关注“东突厥”(即哈萨克与中亚的突厥)。凯末尔对此不感兴趣,只着眼于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现存及历史的文化中的土耳其人。
在20年代,土耳其先后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订了友好条约,并在30年代同希腊建立了友好关系。1932年,希腊首相维尼齐洛斯甚至提名凯末尔为193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选人。
到1938年,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土耳其已经建成了基本的工业体系,工业年增长率达10%,同苏联、德国、日本一道被列为当时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凯末尔充满传奇色彩的不断奋斗和努力下,土耳其不但从被西方列强瓜分宰割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半封建半奴隶制帝国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从一个伊斯兰神权君主制国家变成了议会立宪制共和国;从官僚封建主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走上经济发展正轨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
在1930年代,凯末尔国家主义政策所创造的奇迹不仅为土耳其人所敬佩景仰,而且在波斯、阿富汗、中国、印度等仍然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之苦的东方民族和国家中引起重视,“土耳其模式”成了东方国家救亡图存,摆脱列强压迫的希望之一。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